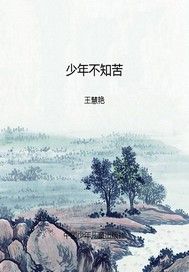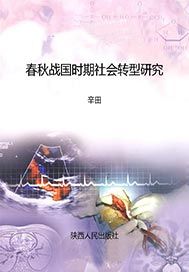第六章 为心中的天堂投资
1
秋末冬初的黄昏来得总是很快,还没等山间被阳光蒸发起的水气消散,太阳就落进西山。山谷中冷飕飕的风将白色雾气赶出山谷,将柿树下一片片干枯的树叶吹向空中,催促得一双双山雀飞向巢窝,西山的阴影,很快倾斜在槐树坡村里。
经过了整天风吹日晒的张金锁的脸膛上,还满是张二九千元价码的喜悦。
“当家的,再给我盛一碗面来。”张金锁在东厢房屋吃饭,他已经吃下满满的两碗面条。平素下他两碗面条就已足够了,有着张二九千元价码的喜悦要再多吃一碗。上竿,他朝田里运肥,活儿不轻,他未感劳累。下午,他赶母猪往邻村配种,母猪极为难赶,活儿也不是轻活,他未感疲乏。他为张二九付出千元就买得张二九发誓一个张字掰不开的喜悦,为他添了无穷的神力,使他认定,他拿得槐树坡支部与村委会的印章不是十分困难。他和张石头已经商定,晚饭后,他与张石头分头活动,一个走访韩美凤,一个去会见杨大年。他们把韩美凤与杨大年看为最难攻下的堡垒,要千方百计不遗余力的尽快达到目的。
张金锁的妻子史梅梅,不满张金锁竞选村支书和村长,而她照常敬张金锁穿,让张金锁吃,她很快端来一碗细溜溜白生生的面条。
“拴虎(张金锁儿子)爹,我再和你有言再先,不要竞选村支书、村长,自己有吃有喝的,足已了,常言说得好知足常乐,为什么放着乐不乐,去找麻烦?”
张金锁耳无妻子的不满,只管转着活灵灵的眼珠琢磨他的“天堂”。今晚,他负责走访韩美凤,他认真地思谋对待韩美凤的招数,一定要四面光滑,八面玲珑。
2
晚饭后,韩美凤还如往天那样忙碌。她婆母的姐姐患病,她的婆母往邻居村去伺候姐姐去了。白冰冰委托她代管的大眼往街上与同学耍去了,她喂完了欢欢食,送走了欢欢的大便,坐在炕沿上喘息。
多少人说欢欢终久要把韩美凤拖垮,欢欢一直还没有清醒的样子,依然是植物人一个。韩美凤依旧不显烦不显躁平平静静。韩美凤的爷爷、奶奶全是渡过江、入过朝的老兵。全是戴过红花受过奖励的英模。韩美凤的爷爷、奶奶复员之后,常常教导韩美凤要学习雷锋,好好作人。韩美凤的丈夫欢欢,也参军多年,在部队里当特种兵,又是雷锋式的好战士。欢欢与韩美凤恋爱之后,留予韩美凤的美好印象,如刻在韩美凤心上,风吹不落,雨洗不掉。欢欢带韩美凤往欢欢舅舅家走亲,欢欢将舅舅家村里一道街的积雪扫尽,欢欢的舅舅就认为欢欢疯了,正儿八经的训斥欢欢:“现在,谁还知道雷锋姓甚叫甚?你还当你的雷锋?快往医院里让大夫瞧瞧,你的神经是不是出了毛病?” 欢欢朝韩美凤叹口气,说:“中国绝不能少了雷锋!” 欢欢依旧以实际行动传播雷锋精神。一天,欢欢陪同韩美凤往五里坡镇赶集,出售韩美凤家多余的红薯,遇上一个光头、一个长发、一个大嘴欺行霸市,不准一个老实厚道的农民在他们的菜摊一侧销售黄瓜,揍得老实厚道的农民倒地不起,还要把老实厚道的农民的两筐黄瓜扔进水沟。欢欢看不过眼,为人解忧的劲头骤然升起,不等“光头”将农民的两筐篮黄瓜扔进水沟,吩咐韩美凤看守着红薯,朝着“光头”猛吼:“你个鬼头小子干什么?!”眨眼间,光头、长发、大嘴张牙舞爪地将欢欢围住。三个家伙同时咆哮:“你这小子想让老子们给你放放血了是不是?”嘴尖舌快的“光头”吼着还猛朝欢欢右肋间狠打一拳。欢欢不得不朝他们动武。他不等光头的拳头收走,他的右脚就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穿着皮鞋的脚尖准确地踢中光头的鼻梁,光头的身子便轻飘飘地斜飞出去。欢欢又不等掏出匕首的“长发”、“大嘴”伸出匕首,身影一晃,啪啪两声闷响,“长发”与“大嘴”齐被放倒,两把明晃晃的匕首都变戏法似的到了欢欢手里。欢欢轻松的把两把匕首像撅筷子似的撅断,扬手扔进远远的水沟里。
“光头”、“长发”、“大嘴”齐溜溜地跪倒在欢欢面前请求饶命,并发誓今后再不敢胡作非为。
韩美凤的婆婆又善良又贤惠,对韩美凤的处境十分同情,不止一次地同韩美凤说:“美凤,你和欢欢离婚算啦,让我一个人跟着她苦。要不,你不乐章舍下我们娘儿俩走,你和韩美凤离了婚,做我的闺女,做欢欢的妹子,招一个女婿来,你还关照我娘儿俩。你老这么苦苦累累的,让我心疼的也受不了哩。” 韩美凤一次次的笑笑说:“妈,也许欢欢还会好的,别着急。” 韩美凤笑得实实在在。
美凤坐在坑沿上喘息三五分钟,转身面向直挺挺地躺在炕上的欢欢,又以她纯真的感情召唤着欢欢苏醒:“欢欢,欢欢,是美凤喊你,你醒醒……”韩美凤一日三次,早一次、午一次、晚一次,不厌其烦,不遗余力,语气如阳光一样温暖,声音似春风一样温柔。她尽情的唤罢,再为欢欢唱出她与欢欢热恋时唱予欢欢的秧歌:
白日里想你纫不上针
黑夜里想你吹不灭灯
白日里想你盼黄昏
黑夜里想你等不到明
枣木擀杖柳木案
饺子包子一串串
一心等着亲人来
眼里落下泪蛋蛋……
韩美凤充满深情的秧歌格外的优美,如红靛吐曲,似百灵鸣歌,带着虹的美丽,含着花的芳香,美得使石头也会微笑,香得让泥土也会绽彩。韩美凤为欢欢唱罢秧歌,扭身往院里走去。而她的双脚刚落地,白冰冰托抚给她的大眼即活蹦乱跳地朝她跑来,扑到她的怀里双手把她的腰搂紧。
“你这个兔崽子,到哪儿耍去来?”韩美凤乐呵呵的说着,拿起笤帚将大眼衣服上和鞋上的泥土扫落。
大眼蹦到炕上,偎依在韩美凤怀里揉一揉湿漉漉的两只大眼不语。
“谁欺负你啦?”韩美凤问大眼。
“谁也没有欺负我,我自己摔了个大马趴,摔得好疼。”
“没出息,摔个大马趴值得两眼里出水儿!”
“你摔个大马趴也得眼里出水儿。”大眼停一停抬起头,双手搂住韩美凤的脖颈,一双精明的眼睛,直巴巴地看着韩美凤不语。大眼的奶奶和母亲丢开大眼入土已经一年之久,白冰冰外出,只要韩美凤不出门,大眼就以韩美凤的家为家,同韩美凤相依为命。韩美凤也特乐意照看讨人喜欢的大眼,只要大眼喊她一声婶儿,她浑身的劳乏就轻而淡之。她轻轻地拍一拍大眼的后背,亲昵地问大眼:
“你鬼崽子瞪着两大眼儿想同我说么?”
“我想我爹回来了,我要和他耍不值。”
“为么耍不值?”
“他一走,就没有我了。”
“你爹怎么能没有你?”
“他要有我,怎么还不回来?”
“你爹快回来了。”
“婶儿,”大眼叫得很甜,没有过的甜,“我又想,我不叫你婶儿了。”
“你不叫我婶儿,叫我么哩?”大眼的口气之甜,甜在韩美凤对他的家。韩美凤桃花般的脸上越发好看。
“我想叫你妈哩。”大眼说得更甜。
“哈哈,你这个兔崽子,”韩美凤在大眼后背上猛拍一掌,“你不要你爹啦?”
“我怎么能不要我爹?你当我妈,我爹还是我爹。”
“不许瞎叫,只能叫我婶儿!”韩美凤严厉地要推开大眼往厅室里去,这时院门被人推开,呐喊美凤在家不?韩美凤急忙将大眼安排到小西屋里睡觉,捷步走向院里,应一声美凤在家,把来人迎接到厅屋,请来人在木椅上坐下,为来人倒一杯开水,她才在另一个木椅上坐下来。
来人是张金锁。
“金锁哥,你可稀罕,喝水,我没烟招待你。”韩美凤不管谁来家串门都很热情,对不常进家的张金锁也不例外。
张金锁伸手掏出纸烟,表示他带来纸烟。他问过欢欢近况,问过韩美凤婆婆去向,立即对韩美凤表示歉意:“美凤,请你原谅我没常往你这儿来走走,对你关心不够。实话实说,我爹躺倒三年才咽气,实在是把我煎熬毛了,我刚把我爹发落了就看你来了。”张金锁喝口开水,不等韩美凤插话,又急忙对韩美凤之艰难表示关心。“美凤,别看我爹把我拴死,没有常到你这里来看看,”他拿着纸烟的手放在胸口上,“我的心和你不远,常同人说你美凤是天下第一!”
“哈哈哈。”韩美凤笑得丽脸越发讨人喜欢,声音也更加好听,“金锁哥,有人说我美凤累的天下第一,有人说我苦的天下第一,有人说傻的天下第一,你说我的天下第一指的是么?”
“我……”张金锁微笑着,“我说你的天下第一:一是人才天下第一;二是人品天下第一。不说你的人才,单说你的人品;谁不说,如果换转个人,也得把欢欢交给欢欢的母亲,鞋底上抹油——溜了。现在,不是雷锋的时代,现在人人看重的是自己,人人把自己看成帝,惟独你美凤,还是雷锋的一副心肠。可以说,当今世界上没有第二个美凤。用毛泽东的话说,你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哈哈哈,”韩美凤又笑得丽脸如花,“金锁哥,看你把我夸的,我只不过是心眼不多就是了。”
“要说,”张金锁思谋着妥当的词儿,不快不慢的说,“要说你心眼不多,你也确实太缺心眼儿,你只要精明一点,就不能不顾一顾自己。好花儿能有几日红?是不是哩?”
韩美凤丽脸上的微笑失落,不由得叹一口气。
张金锁胖乎乎的黑脸上也立即就得阴沉沉的,也紧忙叹一口气。
“美凤,今晚上我到你这儿来,我不只是来同你说两句淡话,让你开一开心,我给你拿来了两万块钱。”张金锁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两沓钱票,放到美凤脸前的桌子上。
韩美凤心里咯噔一下,怔怔地斜一眼两沓钱票,吃惊地倒吸一口气。
“美凤,你不知道,今年春天,我去南边县里看望一个朋友,同朋友一块儿承包下朋友村里一道山沟,开采了几吨铁矿石,朋友就先把十万给我拿来。我内弟急着送他家人住院借去八万。我把这两万给你拿来,用在欢欢身上。你看看欢欢的病还能不能治好,省了你老跟他受苦。”
韩美凤对张金锁谋算好的“天堂”,准备大手为“天堂”投资的事还一点不知。她心中埋藏着爷爷、奶奶两位老革命对她的教育,而她毕竟生活在当今时代里,晓得人的生活的改善,人的道德、信念会有变。她与张金锁未打过多少交道,而她心里有底,张金锁绝不是白冰冰。人不图利不早起,张金锁绝不会没有一图。两沓钱票,不是三二百,张金锁图的么呢?也许没有二图、三图,只有一图。
“金锁哥,”韩美凤又眉开眼笑,平平实实,“ 你也知道我美凤不精明,对谁也不会俏,爱神筒里吞棒槌——直出直入。你为我大手的拿来两万,你一定得有你不便说出口的想法。我由不得猜测你的想法,我要猜得牛头不对马嘴,你可别和我一般见识。”
“你说。”张金锁眯缝着两只眼睛说。
“金锁哥,我猜你不寻常的让我想不到的大手,必定得有一图,你的一图不在欢欢身上,在我美凤身上。”
“你说。”张金锁依然笑眯眯的。
“是看得起我美凤的人才,想让我美凤失身,我要是猜得准确,金锁哥,你就是从门缝里看美凤,把美凤看扁了,韩美凤懂得而今钱的力量很大,力量再大,对我美凤也起不了作用。”
张金锁呼起长出口气,难过得好像吃下黄连,脸色陡然变得灰黄,如同抹满黄酱,眼睛也陡然失去光亮,如同落满灰尘,龇牙咧嘴地站起来,嗖地将两沓钱票抓在手里,通通通地走开。
“金锁哥,你别走。”韩美凤喊。
也许张金锁没有想走开,他还未走到院门口就返回厅室,咚一声在木椅上坐下,难过万分地龇一龇牙咧一咧嘴,将两沓钱票放在桌子上,伸手抹一抹潮湿的眼睛:“美凤,我……我只想你不会把我拿给你这两万块钱看成无价之宝,做梦也没有想到你会把我的好心看成了驴肝肺!我……我只想你会请我吃下两个甜柿子,做梦也想不到你会让我吃下黄连!韩美凤,你真有你的!”
见不了人难过的韩美凤诚恳地向张金锁承认不是:“金锁哥,金锁哥,你看你……俺不是早和你说啦,俺要猜得牛头不对马嘴,你可别跟我一般见识。俺错误地理解了你,请你原谅。”
“你站在山上看张金锁,把张金锁看矬了。”张金锁之显著的难过化解大半,语气也不再带怒,“美凤,你这老哥同你实话实说,你的招人喜爱的人才特招人喜爱,谁都乐意多看你一眼,傻子也对你目不转睛,我心里也特有你的俊美,我只要走过你的门外,就想看你一眼。而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对你绝对没有一点、一滴、一分、一毫的邪念!人的名,树的影,你听哪一个说到我男女关系上有绽?美凤啊,你这老哥对任何人都是一片菩萨心肠。我的心里只有欢欢的不幸,只有你美凤的痛苦!”张金锁末了的每一个字,都如刚刚出水的玛瑙,坚硬而有光洁。
韩美凤心里顿时闪出张金锁家的千年柿树已枯,她马快地跑往院里为张金锁拿来一盘甜甜的红柿,朝张金锁嫣然一笑:“金锁哥,你快吃柿子。”
张金锁随手拿起一个红红的柿子。
“金锁哥,我误解了你的菩萨心肠,错把你的好心看成驴肝肺,也有客观原因。我不爱张扬,你还不知道,”韩美凤絮絮叨叨,如与邻里谈说家常。“不止一个男人,对我明面上说是同情欢欢的不幸,实际上是想占我美凤的便宜,有的拿我二百,有的拿我五百,当然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个乡干部还让我给得罪了。”
张金锁再拿起一个红柿,歉意十足地裂嘴笑笑,“刚才我对你的怪怨,你也别再放在心上。”
韩美凤不在乎的把手一摆,如竹筒里往外倒豆一样痛快:“我要小肠鸡肚,我就不让你吃甜柿子了。”
“哈哈哈。”张金锁以笑带答,笑得嘴张老大,两眼眯成一条细缝,眼光在细缝中飞到左边又飞到右边,仿佛他走过韩美凤门口偷偷的看到韩美凤的姿色一样舒适。
“金锁哥,你再吃一个柿子。”
“我把一盘柿子全吃了。”
“全吃了,是你看得起我。”
“当然看得起你。”张金锁又拿起一个柿子。“你把两万块钱数一数。”
“我不用数。你还把钱拿走。”
“你说什么?”张金锁把拿起的柿子又放下。
“你还把钱拿走。”韩美凤说得清清楚楚,“先一阵,我跟冰冰哥往凤凰岭爱国主义基地去打工,挣下两万块钱。冰冰哥上一次去要没有要到手,又要去了。这一次,我想再不会瞎猫扑老鼠——白跑了。我先花我的两万。有了难的人才知人间情可贵,我这辈子忘不了你的菩萨心肠!”
张金锁张口无声,两眼发滞,脸皮僵木,嘴角微微下垂,露出点滴冷笑,呼吸一阵比一阵急促。他认定,韩美凤给予他红红的柿子,他之图谋就有了百分之六十的把握,哪儿想到……
“美凤,”张金锁两眼望着院门,“你认准冰冰姐夫铁板上钉钉会把欠款要来?”
“我想百分之百的会要来。”
“要是要不来呢?”
“要不来,”韩美凤又如竹筒里往外倒豆,“我再去求你。”
张金锁没有想到这一步,他一时想不妥再如何开口,心里打鼓:“眼下,他妈的只能落到这一步……”
3
张金锁走访韩美凤之家,未能随心所欲,未能钱到成功,心气不顺。张石头负责走访杨大年之家,也并不是马踩平川,顺顺当当,而张石头未失乐观,还信心十足。
张石头得意地想到,他只要保得张金锁拿到槐树坡的两块印章,张金锁心中的“天堂”全部实现,他之报酬将相当丰厚:他可抛开简陋的平房,建起豪华的小别墅;他可扔掉老掉牙的“飞鸽”;买得桑塔纳小车;他要乐意进县城高档饭店吃一吃、住一住、玩一玩三陪小姐,也能够如愿。他吃过晚饭之后,张金锁还未迈进韩美凤的院门,他就走进杨大年的院里。
杨大年的房院与韩美凤家的房院相似,正房坐北朝南,平房五间,四室一厅,西厢房两间,一间做厨房,一间为牛圈。院子约二分余大。杨大年考上大学的女儿和杨大年的内当家均不在家。
“相好的在不?”张石头站在院里朝厅室里喊。
厅室约30多米,宽宽敞敞,而陈设极为简单,只有一张破旧的方桌,两把老式的木椅,一个小小的书架上摆放的书籍不过四五十本,唯一引人注目的是贴在正面墙上的崭新的毛主席画像。厅室里点着油灯,杨大年为供给女儿读书,与内当家舍不得穿舍不得吃,也舍不得安装电灯。杨大年正坐在一个用稻草编制的不过半尺高的铺团上,为编好的一个荆条筐篮进一步加工。张石头在院里喊他相好的在不,他没有应声,他一向不把张石头看在眼里、放在心上。
“相好的在不?”张石头在院里又喊。
“有请。”杨大年答话,嘴唇朝左侧歪一歪答的有声有色,使张石头睁着两只大眼笑呵呵的撩起厅室门帘走进厅室。
张石头在杨大年心目中个头不高,张石头却把杨大年看得高高大大,他同人不止一次的说杨大年是条汉子。前年春天,张石头17岁的女儿朝五里坡镇赶集,天黑后家走,遇上一胖一瘦的两个持匕首的歹徒再难逃脱,拼命地呼唤救命。碰巧被赴五里坡镇赶集的杨大年闯上。力大超人的杨大年一拳使胖歹徒的匕首落地,一脚使瘦歹徒的匕首飞远,杨大看再猛窜一步,很踢一脚,踢得胖歹徒狼狈逃窜,又急转身将瘦歹徒抓住送往派出所。张石头的女儿安全归家之后,将杨大年的勇为告知张石头,张石头立即拿给杨大年两瓶白酒表示感谢,杨大年一瓶酒不留,而后张石头就赞扬杨大年是条汉子。
“噢哟哟,杨大年,现时,人人都用塑料筐篮了,你还用荆条编制筐篮,太保守了吧?”张石头满脸堆笑的说着在一个木椅上坐下来。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杨大年只管为荆条筐篮加工,头不抬起。
“杨大年,从今往后,你在咱们槐树坡村,不,在左右十村八村也是首屈一指了。”张石头说着把老顸的右手大拇指伸给杨大年。
“就凭我编的这荆条筐篮首屈一指了?”
“去年的吧,”张石头张开大嘴笑笑,“你的闺女考一重点大学,再上个台阶就是硕士、博士。博士文凭一拿,也许是科学家,也许是作家。反正你杨大年就成了‘家’的老子,哪一个也就没有你的地位高了,牌面亮了。你的闺女要想进入政界,不过一年半载,不是县长就是书记。你的地位,你的牌面,就更加没人可比了。到时候,我来给你提鞋,你也会嫌我的指头粗哩。是不是?”
杨大年不管张石头如何捧场作戏,他心里也平淡如水。张石头与他瞎掰,他也与张石头扯淡:“要说地位,要论牌位,你石头哥在咱槐树坡才是庙里的旗杆——独一无二。”
“你别瞎掰,我张石头怎么能是庙里的旗杆?”
“你常同人理论的金钱的作用:有钱买得鬼推磨,就是独一无二的高见。咱们村里,不管是喝墨水多的,不管是喝墨水少的,除了你石头哥,谁还会有这高见?……”
“你别瞎掰啦,我那是狗熊念经——瞎说一气。”你给闺女念大学的奖金准备充实没有?他不等杨大年张口,“你手头要是紧巴,金锁哥叫我转告你,他可以先借给你三万两万的花着。”
“金锁哥怎么发啦?”杨大年说着猛抬起头,将荆条筐篮丢开。他仿佛没有想到,又似已有所料,惊喜的双眼瞪圆,下巴伸前。若要细看,难说不是故意为之。
“金锁哥也谈不上发了。”张石头未朝杨大年细看,“你住的离张金锁较远,你还不知道,今年春天,他在南边县里同他一个朋友,承包了一片荒山,开采了两车铁矿石,赚了几万,才把钱拿到。昨天晚上,我同他说起你可能面临困难,他立即就说叫我来转告你,他乐意为你解囊。”
“哈哈,”杨大年笑得极带感激之情。“石头哥,我和金锁哥没多少交往,我还不了解金锁哥会把我的难题放在眼里。当今世风日下,人眼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金锁哥还有当年的老经:先人后已,真让我杨大年感动得、佩服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我告诉你说杨大年,要论为人,金锁哥可以说是真没褒贬。”张石头越说劲头越足,如同推小车的扭动P股——不由自主,砰地拍响大胯,“他和你杨大年可以说是半斤对八两:你喜欢与人为善、助人为乐,他同我说起话来常常说到,人间少了什么,也不能少了雷锋精神。”
“是吗?”杨大年寻找一根纸烟拿给张石头,眉开眼笑着问张石头。
“是我说得毫不含糊!”张石头嗖地挺身而立,如一块高大的石碑,威严而又庄重,“我没有喝过他一杯酒,没抽过他一支烟,我不会给他吹喇叭抬轿子!”
“为他吹喇叭抬轿子也不为丑。”杨大年庄重而严肃的紧接张石头的话,“当今,金锁哥的先人后已的精神很不寻常,完全应该为他吹一吹喇叭,抬一抬轿子。”
“你要这么说,我立刻去见他把钱给你拿来。”
“石头哥,你回来。”杨大年等张石头坐回到木椅上,“我不困难,我的钱攥在手里。”杨大年喘一口气,“白冰冰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讨要我们的打工款去了,第一次去,没有讨要到手,这一次去,绝不会扑空了。”杨大年说得刚劲有力。
“嗬嗬嗬,”张石头笑得目光明丽,满脸开花,朝杨大年伸长脖颈,以嘲笑的口气,“我的老弟,你完全相信白冰冰不会再空手而归?”
“我百分之百的相信,”杨大年故意拧一拧脖颈,挺高胸膛,“我百分之百的相信他会把欠款要回!”
“咱俩打个赌吗?”
“打赌就打赌。”
“白冰冰要不是空手而归,我输你二斤豆腐一斤老白干,要是空手而归呢?”
杨大年嗖地站起,男子汉的劲头十足:“白冰冰要是要不回欠款,我为金锁哥两肋插刀,他东我东,他西我西。”
“君子一言,就这么的!”
秋末冬初的黄昏来得总是很快,还没等山间被阳光蒸发起的水气消散,太阳就落进西山。山谷中冷飕飕的风将白色雾气赶出山谷,将柿树下一片片干枯的树叶吹向空中,催促得一双双山雀飞向巢窝,西山的阴影,很快倾斜在槐树坡村里。
经过了整天风吹日晒的张金锁的脸膛上,还满是张二九千元价码的喜悦。
“当家的,再给我盛一碗面来。”张金锁在东厢房屋吃饭,他已经吃下满满的两碗面条。平素下他两碗面条就已足够了,有着张二九千元价码的喜悦要再多吃一碗。上竿,他朝田里运肥,活儿不轻,他未感劳累。下午,他赶母猪往邻村配种,母猪极为难赶,活儿也不是轻活,他未感疲乏。他为张二九付出千元就买得张二九发誓一个张字掰不开的喜悦,为他添了无穷的神力,使他认定,他拿得槐树坡支部与村委会的印章不是十分困难。他和张石头已经商定,晚饭后,他与张石头分头活动,一个走访韩美凤,一个去会见杨大年。他们把韩美凤与杨大年看为最难攻下的堡垒,要千方百计不遗余力的尽快达到目的。
张金锁的妻子史梅梅,不满张金锁竞选村支书和村长,而她照常敬张金锁穿,让张金锁吃,她很快端来一碗细溜溜白生生的面条。
“拴虎(张金锁儿子)爹,我再和你有言再先,不要竞选村支书、村长,自己有吃有喝的,足已了,常言说得好知足常乐,为什么放着乐不乐,去找麻烦?”
张金锁耳无妻子的不满,只管转着活灵灵的眼珠琢磨他的“天堂”。今晚,他负责走访韩美凤,他认真地思谋对待韩美凤的招数,一定要四面光滑,八面玲珑。
2
晚饭后,韩美凤还如往天那样忙碌。她婆母的姐姐患病,她的婆母往邻居村去伺候姐姐去了。白冰冰委托她代管的大眼往街上与同学耍去了,她喂完了欢欢食,送走了欢欢的大便,坐在炕沿上喘息。
多少人说欢欢终久要把韩美凤拖垮,欢欢一直还没有清醒的样子,依然是植物人一个。韩美凤依旧不显烦不显躁平平静静。韩美凤的爷爷、奶奶全是渡过江、入过朝的老兵。全是戴过红花受过奖励的英模。韩美凤的爷爷、奶奶复员之后,常常教导韩美凤要学习雷锋,好好作人。韩美凤的丈夫欢欢,也参军多年,在部队里当特种兵,又是雷锋式的好战士。欢欢与韩美凤恋爱之后,留予韩美凤的美好印象,如刻在韩美凤心上,风吹不落,雨洗不掉。欢欢带韩美凤往欢欢舅舅家走亲,欢欢将舅舅家村里一道街的积雪扫尽,欢欢的舅舅就认为欢欢疯了,正儿八经的训斥欢欢:“现在,谁还知道雷锋姓甚叫甚?你还当你的雷锋?快往医院里让大夫瞧瞧,你的神经是不是出了毛病?” 欢欢朝韩美凤叹口气,说:“中国绝不能少了雷锋!” 欢欢依旧以实际行动传播雷锋精神。一天,欢欢陪同韩美凤往五里坡镇赶集,出售韩美凤家多余的红薯,遇上一个光头、一个长发、一个大嘴欺行霸市,不准一个老实厚道的农民在他们的菜摊一侧销售黄瓜,揍得老实厚道的农民倒地不起,还要把老实厚道的农民的两筐黄瓜扔进水沟。欢欢看不过眼,为人解忧的劲头骤然升起,不等“光头”将农民的两筐篮黄瓜扔进水沟,吩咐韩美凤看守着红薯,朝着“光头”猛吼:“你个鬼头小子干什么?!”眨眼间,光头、长发、大嘴张牙舞爪地将欢欢围住。三个家伙同时咆哮:“你这小子想让老子们给你放放血了是不是?”嘴尖舌快的“光头”吼着还猛朝欢欢右肋间狠打一拳。欢欢不得不朝他们动武。他不等光头的拳头收走,他的右脚就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穿着皮鞋的脚尖准确地踢中光头的鼻梁,光头的身子便轻飘飘地斜飞出去。欢欢又不等掏出匕首的“长发”、“大嘴”伸出匕首,身影一晃,啪啪两声闷响,“长发”与“大嘴”齐被放倒,两把明晃晃的匕首都变戏法似的到了欢欢手里。欢欢轻松的把两把匕首像撅筷子似的撅断,扬手扔进远远的水沟里。
“光头”、“长发”、“大嘴”齐溜溜地跪倒在欢欢面前请求饶命,并发誓今后再不敢胡作非为。
韩美凤的婆婆又善良又贤惠,对韩美凤的处境十分同情,不止一次地同韩美凤说:“美凤,你和欢欢离婚算啦,让我一个人跟着她苦。要不,你不乐章舍下我们娘儿俩走,你和韩美凤离了婚,做我的闺女,做欢欢的妹子,招一个女婿来,你还关照我娘儿俩。你老这么苦苦累累的,让我心疼的也受不了哩。” 韩美凤一次次的笑笑说:“妈,也许欢欢还会好的,别着急。” 韩美凤笑得实实在在。
美凤坐在坑沿上喘息三五分钟,转身面向直挺挺地躺在炕上的欢欢,又以她纯真的感情召唤着欢欢苏醒:“欢欢,欢欢,是美凤喊你,你醒醒……”韩美凤一日三次,早一次、午一次、晚一次,不厌其烦,不遗余力,语气如阳光一样温暖,声音似春风一样温柔。她尽情的唤罢,再为欢欢唱出她与欢欢热恋时唱予欢欢的秧歌:
白日里想你纫不上针
黑夜里想你吹不灭灯
白日里想你盼黄昏
黑夜里想你等不到明
枣木擀杖柳木案
饺子包子一串串
一心等着亲人来
眼里落下泪蛋蛋……
韩美凤充满深情的秧歌格外的优美,如红靛吐曲,似百灵鸣歌,带着虹的美丽,含着花的芳香,美得使石头也会微笑,香得让泥土也会绽彩。韩美凤为欢欢唱罢秧歌,扭身往院里走去。而她的双脚刚落地,白冰冰托抚给她的大眼即活蹦乱跳地朝她跑来,扑到她的怀里双手把她的腰搂紧。
“你这个兔崽子,到哪儿耍去来?”韩美凤乐呵呵的说着,拿起笤帚将大眼衣服上和鞋上的泥土扫落。
大眼蹦到炕上,偎依在韩美凤怀里揉一揉湿漉漉的两只大眼不语。
“谁欺负你啦?”韩美凤问大眼。
“谁也没有欺负我,我自己摔了个大马趴,摔得好疼。”
“没出息,摔个大马趴值得两眼里出水儿!”
“你摔个大马趴也得眼里出水儿。”大眼停一停抬起头,双手搂住韩美凤的脖颈,一双精明的眼睛,直巴巴地看着韩美凤不语。大眼的奶奶和母亲丢开大眼入土已经一年之久,白冰冰外出,只要韩美凤不出门,大眼就以韩美凤的家为家,同韩美凤相依为命。韩美凤也特乐意照看讨人喜欢的大眼,只要大眼喊她一声婶儿,她浑身的劳乏就轻而淡之。她轻轻地拍一拍大眼的后背,亲昵地问大眼:
“你鬼崽子瞪着两大眼儿想同我说么?”
“我想我爹回来了,我要和他耍不值。”
“为么耍不值?”
“他一走,就没有我了。”
“你爹怎么能没有你?”
“他要有我,怎么还不回来?”
“你爹快回来了。”
“婶儿,”大眼叫得很甜,没有过的甜,“我又想,我不叫你婶儿了。”
“你不叫我婶儿,叫我么哩?”大眼的口气之甜,甜在韩美凤对他的家。韩美凤桃花般的脸上越发好看。
“我想叫你妈哩。”大眼说得更甜。
“哈哈,你这个兔崽子,”韩美凤在大眼后背上猛拍一掌,“你不要你爹啦?”
“我怎么能不要我爹?你当我妈,我爹还是我爹。”
“不许瞎叫,只能叫我婶儿!”韩美凤严厉地要推开大眼往厅室里去,这时院门被人推开,呐喊美凤在家不?韩美凤急忙将大眼安排到小西屋里睡觉,捷步走向院里,应一声美凤在家,把来人迎接到厅屋,请来人在木椅上坐下,为来人倒一杯开水,她才在另一个木椅上坐下来。
来人是张金锁。
“金锁哥,你可稀罕,喝水,我没烟招待你。”韩美凤不管谁来家串门都很热情,对不常进家的张金锁也不例外。
张金锁伸手掏出纸烟,表示他带来纸烟。他问过欢欢近况,问过韩美凤婆婆去向,立即对韩美凤表示歉意:“美凤,请你原谅我没常往你这儿来走走,对你关心不够。实话实说,我爹躺倒三年才咽气,实在是把我煎熬毛了,我刚把我爹发落了就看你来了。”张金锁喝口开水,不等韩美凤插话,又急忙对韩美凤之艰难表示关心。“美凤,别看我爹把我拴死,没有常到你这里来看看,”他拿着纸烟的手放在胸口上,“我的心和你不远,常同人说你美凤是天下第一!”
“哈哈哈。”韩美凤笑得丽脸越发讨人喜欢,声音也更加好听,“金锁哥,有人说我美凤累的天下第一,有人说我苦的天下第一,有人说傻的天下第一,你说我的天下第一指的是么?”
“我……”张金锁微笑着,“我说你的天下第一:一是人才天下第一;二是人品天下第一。不说你的人才,单说你的人品;谁不说,如果换转个人,也得把欢欢交给欢欢的母亲,鞋底上抹油——溜了。现在,不是雷锋的时代,现在人人看重的是自己,人人把自己看成帝,惟独你美凤,还是雷锋的一副心肠。可以说,当今世界上没有第二个美凤。用毛泽东的话说,你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哈哈哈,”韩美凤又笑得丽脸如花,“金锁哥,看你把我夸的,我只不过是心眼不多就是了。”
“要说,”张金锁思谋着妥当的词儿,不快不慢的说,“要说你心眼不多,你也确实太缺心眼儿,你只要精明一点,就不能不顾一顾自己。好花儿能有几日红?是不是哩?”
韩美凤丽脸上的微笑失落,不由得叹一口气。
张金锁胖乎乎的黑脸上也立即就得阴沉沉的,也紧忙叹一口气。
“美凤,今晚上我到你这儿来,我不只是来同你说两句淡话,让你开一开心,我给你拿来了两万块钱。”张金锁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两沓钱票,放到美凤脸前的桌子上。
韩美凤心里咯噔一下,怔怔地斜一眼两沓钱票,吃惊地倒吸一口气。
“美凤,你不知道,今年春天,我去南边县里看望一个朋友,同朋友一块儿承包下朋友村里一道山沟,开采了几吨铁矿石,朋友就先把十万给我拿来。我内弟急着送他家人住院借去八万。我把这两万给你拿来,用在欢欢身上。你看看欢欢的病还能不能治好,省了你老跟他受苦。”
韩美凤对张金锁谋算好的“天堂”,准备大手为“天堂”投资的事还一点不知。她心中埋藏着爷爷、奶奶两位老革命对她的教育,而她毕竟生活在当今时代里,晓得人的生活的改善,人的道德、信念会有变。她与张金锁未打过多少交道,而她心里有底,张金锁绝不是白冰冰。人不图利不早起,张金锁绝不会没有一图。两沓钱票,不是三二百,张金锁图的么呢?也许没有二图、三图,只有一图。
“金锁哥,”韩美凤又眉开眼笑,平平实实,“ 你也知道我美凤不精明,对谁也不会俏,爱神筒里吞棒槌——直出直入。你为我大手的拿来两万,你一定得有你不便说出口的想法。我由不得猜测你的想法,我要猜得牛头不对马嘴,你可别和我一般见识。”
“你说。”张金锁眯缝着两只眼睛说。
“金锁哥,我猜你不寻常的让我想不到的大手,必定得有一图,你的一图不在欢欢身上,在我美凤身上。”
“你说。”张金锁依然笑眯眯的。
“是看得起我美凤的人才,想让我美凤失身,我要是猜得准确,金锁哥,你就是从门缝里看美凤,把美凤看扁了,韩美凤懂得而今钱的力量很大,力量再大,对我美凤也起不了作用。”
张金锁呼起长出口气,难过得好像吃下黄连,脸色陡然变得灰黄,如同抹满黄酱,眼睛也陡然失去光亮,如同落满灰尘,龇牙咧嘴地站起来,嗖地将两沓钱票抓在手里,通通通地走开。
“金锁哥,你别走。”韩美凤喊。
也许张金锁没有想走开,他还未走到院门口就返回厅室,咚一声在木椅上坐下,难过万分地龇一龇牙咧一咧嘴,将两沓钱票放在桌子上,伸手抹一抹潮湿的眼睛:“美凤,我……我只想你不会把我拿给你这两万块钱看成无价之宝,做梦也没有想到你会把我的好心看成了驴肝肺!我……我只想你会请我吃下两个甜柿子,做梦也想不到你会让我吃下黄连!韩美凤,你真有你的!”
见不了人难过的韩美凤诚恳地向张金锁承认不是:“金锁哥,金锁哥,你看你……俺不是早和你说啦,俺要猜得牛头不对马嘴,你可别跟我一般见识。俺错误地理解了你,请你原谅。”
“你站在山上看张金锁,把张金锁看矬了。”张金锁之显著的难过化解大半,语气也不再带怒,“美凤,你这老哥同你实话实说,你的招人喜爱的人才特招人喜爱,谁都乐意多看你一眼,傻子也对你目不转睛,我心里也特有你的俊美,我只要走过你的门外,就想看你一眼。而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对你绝对没有一点、一滴、一分、一毫的邪念!人的名,树的影,你听哪一个说到我男女关系上有绽?美凤啊,你这老哥对任何人都是一片菩萨心肠。我的心里只有欢欢的不幸,只有你美凤的痛苦!”张金锁末了的每一个字,都如刚刚出水的玛瑙,坚硬而有光洁。
韩美凤心里顿时闪出张金锁家的千年柿树已枯,她马快地跑往院里为张金锁拿来一盘甜甜的红柿,朝张金锁嫣然一笑:“金锁哥,你快吃柿子。”
张金锁随手拿起一个红红的柿子。
“金锁哥,我误解了你的菩萨心肠,错把你的好心看成驴肝肺,也有客观原因。我不爱张扬,你还不知道,”韩美凤絮絮叨叨,如与邻里谈说家常。“不止一个男人,对我明面上说是同情欢欢的不幸,实际上是想占我美凤的便宜,有的拿我二百,有的拿我五百,当然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个乡干部还让我给得罪了。”
张金锁再拿起一个红柿,歉意十足地裂嘴笑笑,“刚才我对你的怪怨,你也别再放在心上。”
韩美凤不在乎的把手一摆,如竹筒里往外倒豆一样痛快:“我要小肠鸡肚,我就不让你吃甜柿子了。”
“哈哈哈。”张金锁以笑带答,笑得嘴张老大,两眼眯成一条细缝,眼光在细缝中飞到左边又飞到右边,仿佛他走过韩美凤门口偷偷的看到韩美凤的姿色一样舒适。
“金锁哥,你再吃一个柿子。”
“我把一盘柿子全吃了。”
“全吃了,是你看得起我。”
“当然看得起你。”张金锁又拿起一个柿子。“你把两万块钱数一数。”
“我不用数。你还把钱拿走。”
“你说什么?”张金锁把拿起的柿子又放下。
“你还把钱拿走。”韩美凤说得清清楚楚,“先一阵,我跟冰冰哥往凤凰岭爱国主义基地去打工,挣下两万块钱。冰冰哥上一次去要没有要到手,又要去了。这一次,我想再不会瞎猫扑老鼠——白跑了。我先花我的两万。有了难的人才知人间情可贵,我这辈子忘不了你的菩萨心肠!”
张金锁张口无声,两眼发滞,脸皮僵木,嘴角微微下垂,露出点滴冷笑,呼吸一阵比一阵急促。他认定,韩美凤给予他红红的柿子,他之图谋就有了百分之六十的把握,哪儿想到……
“美凤,”张金锁两眼望着院门,“你认准冰冰姐夫铁板上钉钉会把欠款要来?”
“我想百分之百的会要来。”
“要是要不来呢?”
“要不来,”韩美凤又如竹筒里往外倒豆,“我再去求你。”
张金锁没有想到这一步,他一时想不妥再如何开口,心里打鼓:“眼下,他妈的只能落到这一步……”
3
张金锁走访韩美凤之家,未能随心所欲,未能钱到成功,心气不顺。张石头负责走访杨大年之家,也并不是马踩平川,顺顺当当,而张石头未失乐观,还信心十足。
张石头得意地想到,他只要保得张金锁拿到槐树坡的两块印章,张金锁心中的“天堂”全部实现,他之报酬将相当丰厚:他可抛开简陋的平房,建起豪华的小别墅;他可扔掉老掉牙的“飞鸽”;买得桑塔纳小车;他要乐意进县城高档饭店吃一吃、住一住、玩一玩三陪小姐,也能够如愿。他吃过晚饭之后,张金锁还未迈进韩美凤的院门,他就走进杨大年的院里。
杨大年的房院与韩美凤家的房院相似,正房坐北朝南,平房五间,四室一厅,西厢房两间,一间做厨房,一间为牛圈。院子约二分余大。杨大年考上大学的女儿和杨大年的内当家均不在家。
“相好的在不?”张石头站在院里朝厅室里喊。
厅室约30多米,宽宽敞敞,而陈设极为简单,只有一张破旧的方桌,两把老式的木椅,一个小小的书架上摆放的书籍不过四五十本,唯一引人注目的是贴在正面墙上的崭新的毛主席画像。厅室里点着油灯,杨大年为供给女儿读书,与内当家舍不得穿舍不得吃,也舍不得安装电灯。杨大年正坐在一个用稻草编制的不过半尺高的铺团上,为编好的一个荆条筐篮进一步加工。张石头在院里喊他相好的在不,他没有应声,他一向不把张石头看在眼里、放在心上。
“相好的在不?”张石头在院里又喊。
“有请。”杨大年答话,嘴唇朝左侧歪一歪答的有声有色,使张石头睁着两只大眼笑呵呵的撩起厅室门帘走进厅室。
张石头在杨大年心目中个头不高,张石头却把杨大年看得高高大大,他同人不止一次的说杨大年是条汉子。前年春天,张石头17岁的女儿朝五里坡镇赶集,天黑后家走,遇上一胖一瘦的两个持匕首的歹徒再难逃脱,拼命地呼唤救命。碰巧被赴五里坡镇赶集的杨大年闯上。力大超人的杨大年一拳使胖歹徒的匕首落地,一脚使瘦歹徒的匕首飞远,杨大看再猛窜一步,很踢一脚,踢得胖歹徒狼狈逃窜,又急转身将瘦歹徒抓住送往派出所。张石头的女儿安全归家之后,将杨大年的勇为告知张石头,张石头立即拿给杨大年两瓶白酒表示感谢,杨大年一瓶酒不留,而后张石头就赞扬杨大年是条汉子。
“噢哟哟,杨大年,现时,人人都用塑料筐篮了,你还用荆条编制筐篮,太保守了吧?”张石头满脸堆笑的说着在一个木椅上坐下来。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杨大年只管为荆条筐篮加工,头不抬起。
“杨大年,从今往后,你在咱们槐树坡村,不,在左右十村八村也是首屈一指了。”张石头说着把老顸的右手大拇指伸给杨大年。
“就凭我编的这荆条筐篮首屈一指了?”
“去年的吧,”张石头张开大嘴笑笑,“你的闺女考一重点大学,再上个台阶就是硕士、博士。博士文凭一拿,也许是科学家,也许是作家。反正你杨大年就成了‘家’的老子,哪一个也就没有你的地位高了,牌面亮了。你的闺女要想进入政界,不过一年半载,不是县长就是书记。你的地位,你的牌面,就更加没人可比了。到时候,我来给你提鞋,你也会嫌我的指头粗哩。是不是?”
杨大年不管张石头如何捧场作戏,他心里也平淡如水。张石头与他瞎掰,他也与张石头扯淡:“要说地位,要论牌位,你石头哥在咱槐树坡才是庙里的旗杆——独一无二。”
“你别瞎掰,我张石头怎么能是庙里的旗杆?”
“你常同人理论的金钱的作用:有钱买得鬼推磨,就是独一无二的高见。咱们村里,不管是喝墨水多的,不管是喝墨水少的,除了你石头哥,谁还会有这高见?……”
“你别瞎掰啦,我那是狗熊念经——瞎说一气。”你给闺女念大学的奖金准备充实没有?他不等杨大年张口,“你手头要是紧巴,金锁哥叫我转告你,他可以先借给你三万两万的花着。”
“金锁哥怎么发啦?”杨大年说着猛抬起头,将荆条筐篮丢开。他仿佛没有想到,又似已有所料,惊喜的双眼瞪圆,下巴伸前。若要细看,难说不是故意为之。
“金锁哥也谈不上发了。”张石头未朝杨大年细看,“你住的离张金锁较远,你还不知道,今年春天,他在南边县里同他一个朋友,承包了一片荒山,开采了两车铁矿石,赚了几万,才把钱拿到。昨天晚上,我同他说起你可能面临困难,他立即就说叫我来转告你,他乐意为你解囊。”
“哈哈,”杨大年笑得极带感激之情。“石头哥,我和金锁哥没多少交往,我还不了解金锁哥会把我的难题放在眼里。当今世风日下,人眼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金锁哥还有当年的老经:先人后已,真让我杨大年感动得、佩服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我告诉你说杨大年,要论为人,金锁哥可以说是真没褒贬。”张石头越说劲头越足,如同推小车的扭动P股——不由自主,砰地拍响大胯,“他和你杨大年可以说是半斤对八两:你喜欢与人为善、助人为乐,他同我说起话来常常说到,人间少了什么,也不能少了雷锋精神。”
“是吗?”杨大年寻找一根纸烟拿给张石头,眉开眼笑着问张石头。
“是我说得毫不含糊!”张石头嗖地挺身而立,如一块高大的石碑,威严而又庄重,“我没有喝过他一杯酒,没抽过他一支烟,我不会给他吹喇叭抬轿子!”
“为他吹喇叭抬轿子也不为丑。”杨大年庄重而严肃的紧接张石头的话,“当今,金锁哥的先人后已的精神很不寻常,完全应该为他吹一吹喇叭,抬一抬轿子。”
“你要这么说,我立刻去见他把钱给你拿来。”
“石头哥,你回来。”杨大年等张石头坐回到木椅上,“我不困难,我的钱攥在手里。”杨大年喘一口气,“白冰冰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讨要我们的打工款去了,第一次去,没有讨要到手,这一次去,绝不会扑空了。”杨大年说得刚劲有力。
“嗬嗬嗬,”张石头笑得目光明丽,满脸开花,朝杨大年伸长脖颈,以嘲笑的口气,“我的老弟,你完全相信白冰冰不会再空手而归?”
“我百分之百的相信,”杨大年故意拧一拧脖颈,挺高胸膛,“我百分之百的相信他会把欠款要回!”
“咱俩打个赌吗?”
“打赌就打赌。”
“白冰冰要不是空手而归,我输你二斤豆腐一斤老白干,要是空手而归呢?”
杨大年嗖地站起,男子汉的劲头十足:“白冰冰要是要不回欠款,我为金锁哥两肋插刀,他东我东,他西我西。”
“君子一言,就这么的!”
-
更多
编辑推荐
- 1一分钟心理控制术
- 2赢利型股民、基民必备全书
- 3人人都爱心理学:最妙...
- 4看图炒股
- 5一看就懂的股市赚钱图形
- 6基金投资最常遇到的1...
- 7买基金、炒股票就这几招
- 8明明白白买基金、炒股票
- 9新手上路 实战股市
- 10少年不知愁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