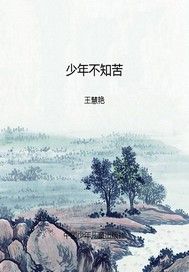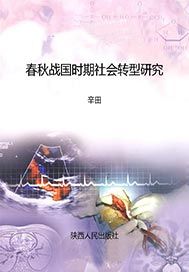第七节 多给自己留几条退路
曾国藩本来是一个崇信程朱理学的学者,不幸的是那个时代把他造就成了一代中兴名将。从1852年奉旨兴办团练开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二年,他一直在过问军事。他仿照明代戚继光创建了一支不同于绿营军(官兵)的新型军队,这支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正当它处于威震四海的顶峰时期,曾国藩下令解散它。他为朝廷创建了一支军队,却为自己解散了这支军队。
曾国藩自从“别开生面,赤地新立”拉起一支从团练改编而成的军队——湘军时,便汹汹然地冲在对抗太平天国的最前列,此时他完全被维护皇朝的义务感和炫耀自己的功业心交融在一起。但在以后的征战生涯中,不仅战事棘手,屡屡受挫,而且也时常受到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谓身陷炼狱,倍尝艰辛,但他毕竟都竭蹶经营,“咬牙立志”地坚持了下来。在1857年回家守制时,他深深反省了自己率湘军出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后来在写给弟弟的信中曾有所提及:
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因此,当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时,则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功高震主的问题。有鉴于此,他将周公旦视为自己的楷模,时常提醒自己以李德裕、霍光等人专横跋扈而不得善终为戒。由此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在出任两江总督兼节制四省军务以后,对如此高位重权却显得喜不胜忧。曾国藩在日记中披露了他的真实心迹:
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负乘之咎也。
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他更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封建统治术。只有推美让功,才能持泰保盈。
当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可五万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下,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在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问题上,更引起他的警觉,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桢而压抑自己,使之处于极难的处境之中。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表露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去年三、四月间,吾兄弟正方万分艰窘,户部尤将江西厘金拨去,金陵围师几将决裂,共事诸公易致龃龉,稍露声色,群讥以为恃功骄蹇。
在这里,曾国藩并非教条的固守畏盈之心,亦非完全杞人忧天,因为他已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清朝二百年来权势最大的汉人,一举一动都将引来众人的瞩目与猜忌。他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道:
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
曾国藩十分了解其弟曾国荃的秉性:精力充沛,有谋有勇,敢作敢为,愿为人先。同时又不失骄纵、蛮横。随其势力逐渐扩大曾国藩愈益为他担心,唯恐其稍有不慎,而酿出祸患。因此,在天下瞩目的天京战役上,曾国藩苦口婆心,提醒曾国荃要慎而又慎。
这些外界的谣言,曾国藩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不行,最忌才能,早已讨厌曾国藩这班书生风头太健,常思惩之。清军中有一位高级将领,名叫胜保,每战必败,每败必保,时人称之为“败保”。他最讨厌曾国藩兄弟。蔡寿祺跟胜保最久,所以他首先弹劾曾国藩,曾国藩先裁湘军,以免授人以柄,就是这个关系。
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对于如何处理大功后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天京陷落的消息传至安庆以后,他更是绕室彷徨,彻夜思考,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预测并做出相应的处理办法。
当曾国藩从安庆赶到江宁的时候,持盈保泰的解决方案已完全成熟。
于是,他在湘军声威达于极盛之时,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明白表示无挟军权自重的态度。
然而,他持盈保泰,裁军“自抑”,而非裁军“自灭”。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五百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文,裁兵费早已筹妥了。
裁兵经费筹妥了,裁兵办法拟好了,只等胜利的莅临。1864年6月16日攻下天京,七月初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二万五千人,随后亦略有裁遣。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以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这也是他强人之处。
曾国藩裁军不辞官,在攻破天京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爵位。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任疆圻,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心怀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制,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要是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忽然为一群图谋不逞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道如何应付,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名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分的恐惧,以为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这时的曾国藩,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柄,一方面更留在两江总督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决不轻言去留,无疑正是使清政府绝对感觉放心的最好办法。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至此,我们当然要相信曾国藩之功成不居与远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贯作风了。
裁撤湘军,曾国藩谋事在先,“盛时常做衰时想”的一个典型事件。
曾国藩一贯主张:“盛时常做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
曾国藩自从“别开生面,赤地新立”拉起一支从团练改编而成的军队——湘军时,便汹汹然地冲在对抗太平天国的最前列,此时他完全被维护皇朝的义务感和炫耀自己的功业心交融在一起。但在以后的征战生涯中,不仅战事棘手,屡屡受挫,而且也时常受到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谓身陷炼狱,倍尝艰辛,但他毕竟都竭蹶经营,“咬牙立志”地坚持了下来。在1857年回家守制时,他深深反省了自己率湘军出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后来在写给弟弟的信中曾有所提及:
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因此,当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时,则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功高震主的问题。有鉴于此,他将周公旦视为自己的楷模,时常提醒自己以李德裕、霍光等人专横跋扈而不得善终为戒。由此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在出任两江总督兼节制四省军务以后,对如此高位重权却显得喜不胜忧。曾国藩在日记中披露了他的真实心迹:
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负乘之咎也。
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他更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封建统治术。只有推美让功,才能持泰保盈。
当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可五万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下,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在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问题上,更引起他的警觉,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桢而压抑自己,使之处于极难的处境之中。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表露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去年三、四月间,吾兄弟正方万分艰窘,户部尤将江西厘金拨去,金陵围师几将决裂,共事诸公易致龃龉,稍露声色,群讥以为恃功骄蹇。
在这里,曾国藩并非教条的固守畏盈之心,亦非完全杞人忧天,因为他已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清朝二百年来权势最大的汉人,一举一动都将引来众人的瞩目与猜忌。他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道:
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
曾国藩十分了解其弟曾国荃的秉性:精力充沛,有谋有勇,敢作敢为,愿为人先。同时又不失骄纵、蛮横。随其势力逐渐扩大曾国藩愈益为他担心,唯恐其稍有不慎,而酿出祸患。因此,在天下瞩目的天京战役上,曾国藩苦口婆心,提醒曾国荃要慎而又慎。
这些外界的谣言,曾国藩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不行,最忌才能,早已讨厌曾国藩这班书生风头太健,常思惩之。清军中有一位高级将领,名叫胜保,每战必败,每败必保,时人称之为“败保”。他最讨厌曾国藩兄弟。蔡寿祺跟胜保最久,所以他首先弹劾曾国藩,曾国藩先裁湘军,以免授人以柄,就是这个关系。
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对于如何处理大功后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天京陷落的消息传至安庆以后,他更是绕室彷徨,彻夜思考,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预测并做出相应的处理办法。
当曾国藩从安庆赶到江宁的时候,持盈保泰的解决方案已完全成熟。
于是,他在湘军声威达于极盛之时,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明白表示无挟军权自重的态度。
然而,他持盈保泰,裁军“自抑”,而非裁军“自灭”。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五百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文,裁兵费早已筹妥了。
裁兵经费筹妥了,裁兵办法拟好了,只等胜利的莅临。1864年6月16日攻下天京,七月初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二万五千人,随后亦略有裁遣。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以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这也是他强人之处。
曾国藩裁军不辞官,在攻破天京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爵位。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任疆圻,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心怀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制,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要是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忽然为一群图谋不逞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道如何应付,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名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分的恐惧,以为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这时的曾国藩,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柄,一方面更留在两江总督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决不轻言去留,无疑正是使清政府绝对感觉放心的最好办法。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至此,我们当然要相信曾国藩之功成不居与远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贯作风了。
裁撤湘军,曾国藩谋事在先,“盛时常做衰时想”的一个典型事件。
曾国藩一贯主张:“盛时常做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
-
更多
编辑推荐
- 1一分钟心理控制术
- 2赢利型股民、基民必备全书
- 3人人都爱心理学:最妙...
- 4看图炒股
- 5一看就懂的股市赚钱图形
- 6基金投资最常遇到的1...
- 7买基金、炒股票就这几招
- 8明明白白买基金、炒股票
- 9新手上路 实战股市
- 10少年不知愁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