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极地寒流过后,村里一片的残枝败叶里冒出了一树的欣欣向荣,春天终于来了。
想写这篇文是一月刚刚过去,二月初的时候。窗外的天空总是阴沉沉的,风也刮得紧,真好像有点儿“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意思。作文刚刚开了头,题目也还没想好,还真就来了个名副其实的极地寒流。零下十几度,还停水断电的。寒流过后,还得忙着打扫残局,写文的事就不得不搁下来了。
今天,是春分,2021年3月20日星期六,辛丑年(牛年)二月初八。以下是我2019年这个时候在休市日本花园拍的一段视频。好一派。。乾坤平分昼夜,却是燕子来时。水边新绿野草,陌上桀然花枝(诗句摘自网络)。。
我坐在窗下的书桌前,面对着电脑屏幕,想着这过去不久,岁末年初的几个月里,有多少亲朋反目,家庭分裂。还有至新冠Pandemic以来,美国仇华,排华暗流涌动,暴力抢劫枪杀。。又有多少人忧心重重,义愤填膺,彻夜难眠。 不免思绪起伏,就想着要把这篇文继续写下去。。
恰逢城里王府正在热火朝天地搞“我的第一次”写作活动,于是来了灵感,这篇作文的题目何不叫着,《家里第一次, 台湾来人了》,更准确点说,是我家第一位从台湾来的客人,一位台湾外省人,祖籍江苏扬州。
他,我称为Q伯,是一位相貌端庄,戴着副金丝边眼镜,身材高大,腰背挺直的国民党退休军人,一位善良睿智,心灵手巧,曽经的资深空军机械师。见到了Q伯,方才恍然大悟,多少年来,被妖魔化的所谓“蒋匪帮,国民党反动派”,其实只是中国平常百姓人家的儿子,兄长,父亲。。
文革后,国门开启。80年代初,家里先后从美国,香港回来了小叔和大嬢。。想来我家老爸久病煎熬中,支持他活着的信念之一,就是想再见一面,49年后一别,就再未相见的亲人。虽然老爸走得太早了,但还是有福的。他是在满足了他心愿的第二年里,也就是见过了比美国小叔迟一年来探亲的香港大嬢后,才过世的。然而Q伯还有许许多多,因着各种原因离开了故土的游子,却没有我家老爸的幸运。。
后来,自己也走到了天涯海角。当读到龙应台的那句“所有的顛沛流離,最後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離死別,都發生在某一個車站、碼頭。上了船,就是一生。”

就想起Q伯和他的父母被分隔在海峡两岸,生死离别近四十年,于是有了更深的体会和感慨。。真是切齿痛恨那些拆散亲情骨肉,导致亲人不能团圆,天人永隔,惨无人道,嗜血残忍,肮脏的政客和政治,人为的斗争和灾难。。
48年南京下关老火车站一别,Q伯正是风华正茂,再归来时已是两鬓斑白,年逾古稀。而他那慈祥的老父老母望穿了秋水,也没能盼到与自己的爱儿再见一面。等到孝子终于再踏上故土,也只能是长跪在安徽异乡僻壤间,两座清草萋萋的土坟外,香烟袅袅,伤心欲绝,热泪长流。。
侯德健 - 歸去來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reload=9&v=N5fSWc-Rsrw
记得第一次见到Q伯时是1987年,大陆台湾刚恢复民间往来不久。是个南京忽冷忽热,天气变化无常的季节(倒是很像休斯顿一,二月的气候,昨日寒冬,今天夏日地来回折腾)。那时候,我家已从老宅搬到母亲单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分配给她的小区楼房里了。
那是个一扫前几日寒冷,阳光明媚,暖和的大晴天,我在三楼家里的阳台上晒被子,远远看到小区主干道上,一群孩子们簇拥在一高一矮的两位男士前后,叽叽喳喳地往我家的方向走来。等他们走近了,我才看清楚,难怪孩子们跟着呢,原来两男士中,那位身材高大的,穿着件三四十年代里的长袍马褂,头上还戴着顶合配的旧时礼帽,活脱脱像一个老电影里走出来的旧时人物。只见他们一行人进了我家这几栋楼的院门。
我回到屋里,没一会儿,就听见楼梯上的脚步,然后是门上的轻叩声。母亲在客厅看书,听见了,就起身去开门。我听见母亲和来人说话,接着是压抑的哭泣声。我赶紧也迎了出去。泪水涟涟的母亲正在把两位眼眶红红的客人(正是我在阳台上看见的那两位男士)往客厅里让,一边哽咽地吩咐我给小朋友们拿糖,谢谢他们热心带路。孩子们拿了糖,很有礼貌地和屋里的人说了再见,都高高兴兴下楼回家去了。
我赶紧去厨房沏了江苏茅山的新茶。两位客人见我端茶来,都站起身来接茶。我是小辈,他们真是太客气了。那位小个子先生对我笑着说,“小溪啊,多年不见了,你长这么高,成了大人啦。”我仔细端详他,认出他是Q公公和Q婆婆的那位在下关当中学老师的外甥,赶紧问候他。我下乡后的那个冬天,派出所那位复原军人L所长和居委会的黑皮主任,一起逼着Q公公和Q婆婆搬离了老宅,把他们赶到安徽水利工地上的小儿子家去了。我心里匆匆一过,真是光阴似箭啊,与两老的这位外甥已近二十年没见过面了。
那天,Q公公和Q婆婆(以下就称公公婆婆,我们从小到大的叫法)的外甥是陪伴他的表哥,那位高个子先生,公公和婆婆在台湾的长子Q伯(比我妈略年长一些)特意登门来探望我母亲的。Q伯接了我手中的茶杯,放在茶几上后,并不坐下,而是拉着我的手,满口扬州乡音,亲切地和我说话。。记得他是谢谢我帮着我妈照顾他的父母。母亲自两位客人进门,就一直止不住流泪,听Q伯这样说就赶紧插话,说以前自己工作忙(我外公外婆去世早,我爸又好多年在外地上班),我和姐年幼时,都是公公,婆婆在帮忙照看。
文革前,公公,婆婆和我家在那条民国路的老宅里,同住了约十年左右。因为57年我家搬进老宅时,老宅里还有空着的房间。征得房主(我妈的堂姐二伯伯)的同意,母亲就邀请了原南京老中央医院里的老前辈,老朋友,Q老先生和他的夫人来同住。
那天妈和我详细地给Q伯叙述了很多他父母生前的事。我主要说的是公公,婆婆对我姐妹从小的关爱,比如我上初一的时候,我爸被学院送去上政校,我妈下乡去四清,我姐上中学住校,我在学校包全伙,一人晚上在家睡觉害怕。每晚都是婆婆过来陪我睡觉。我和姐的毛衣大部分都是婆婆帮我们织的,更是吃过无数次婆婆烹调的美味佳肴。。
Q伯仔仔细细地听我讲着,然后说那也要替他的女儿谢谢我,因为我替公公和婆婆那位从未见过面,比我小两岁,在台湾出生的孙女儿在老人膝下承欢。。他说着,声音颤抖,泪如雨下。。

49年前,Q老先生(公公)在南京老中央医院工作时,是管理财务和总务的负责人。老先生写得一手王羲之体,娟秀的好字,他兢兢业业,精打细算,在医院勤奋工作了大半辈子。尤其是抗战期间,在重庆艰苦的岁月里,用非常有限的资金把医院还有附属护校里医生护士,老师学生员工的衣食住行,安排打理得井井有条,多年受到医院上下同仁们的一致敬爱。
“Q妈妈”(婆婆)是旧时老中央医院里我母亲那辈人对Q老先生夫人一致的爱称。她对医院里年轻辈的医生护士,老师学生们一视同仁,视为己出,总是尽心尽力地关心照顾他(她)们。“Q妈妈”烧得一手好淮阳菜,她还有神奇的本领把粗陋的食材烧成了山珍海味。公公,婆婆家当年的饭桌上即有德高望重的医院院长,资深外科大拿第一刀,也有我妈这样的护校小先生,还有我妈护校里的一帮学生们。当年我爸肺结核病重,能在重庆老中央医院养病痊愈,其中就有婆婆隔三岔五喂养他营养饭食的功劳。
文革前,原南京中央医院里的那些专家权威,老朋友们常来老宅探望公公和婆婆,他们大部分都是着解放军军装的,老中央医院49年后被接管为南京军区总院。尤其是到了过年,公公婆婆的客人更是是络绎不绝。他们来看望公公婆婆,也会来我家坐坐。其中我见过有抗战时期,原中央医院撤退至重庆时的老院长沈克非教授(去北京开会,路过南京),总院留美的热带病专家(城里Alabama 兄的岳父),留美的牙科博士(我发小的父亲),留英的骨科主任。。
后来文革了,公公一辈子只是一名普通的医院职员,49年前,没有留过洋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历史清白简单。49年后早早退了休,本应该是摊不上什么事的。然而过去常来看望他的老朋友们,那些医学界精英们在文革中却无一逃脱被审查迫害的命运。来找公公外调的人多了,这就引起了派出所那位片儿警(后来升了所长)的注意,查了一下,公公家竟然还有一个在台湾的长子,心里不禁大喜,打起了如意算盘。。他出了派出所大门,直奔居委会黑皮主任家而去。。
未完待续
原创拙文,请勿转载,谢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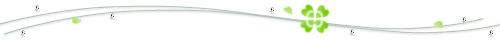
小溪手机随拍,无任何摄影技巧含量,只为自己记录存档~上帝创造大自然和生命的神奇,和心悦的瞬间,以下是新西兰一瞥。下面的两张雪景,是从南岛往北岛路途中,所遇那年春天里,最后一场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