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领导人对亚非领导人施展他们令人印象深刻的友好感情时,他们会发表响亮的关于友谊,平等,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讲话,但是中国在亚洲非洲的行为却常常暴露这些感情的虚伪性,这很难不让人觉得,即使今天,中国还是把这些来访者当成是进贡的臣属之国。当西哈努克王子每年到北京朝奉,赞扬中国的成就并向中国表忠心,这种传统的模式很明显。
当中国要拒绝某些与中国有争议的国家或个人的交往意图的时候,传统模式也会表现出来,旧的傲慢会以他们语言里的粗鲁的暴力来表达。当中国拒绝欲寻求越南问题和平解决的前英国外交大臣高登沃克(Patrick Gordon-Walker)的签证申请的时候,人民日报宣称,中国向他关上了大门。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则被告知,北京不欢迎他,“显然,他敲错了门。”在讨论向安理会提交所谓新殖民主义国家马来西亚问题时,中国说:“这就像在你头上拉屎,同时把刀对着你脖子。”赫鲁晓夫被称为小丑,威尔逊(英国首相)是蠢货(nitwit),其政府是美国心甘情愿的皮条客,林登约翰逊是傻子(driveler),新的苏联领导人则是“魔鬼”,一小撮“可怜虫”(wretches)。
中文专家为这些过激言辞辩解的借口是,中国文学传统之一就是在表达某种心情的时候,倾向于加重语气,这类激烈的词语不能按字面去理解。但是另一方面,一位来访的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人民日报的一位编辑,他得到的回答是很真诚的保证,这些侮辱性的语言不是随便挑选的,而是经过认真的讨论,这些形容词有很仔细排列的等级,“比如,我们决不会称英国首相是‘匪徒’,那个称呼是专门留给美国总统的。”
我怀疑,这种粗鲁的语言的最好解释,还是出于同样的优越感,对于蛮人,自然应该用野蛮的语言。1844年广州的一些横幅就能说明问题:“我们的恨已经白热化,假如我们不彻底消灭你们这帮猪狗,我们就不是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我们一定要杀死你们,割你们的头,把你们烧成灰烬,剥你们的皮,吃你们的肉,让你们知道我们的厉害。”
“我们可以使用文明语言,但是既然你们这些禽兽不通文字,因此我们只能使用粗俗语言来教训你们。”
直到1965年初期,中国似乎在争取亚非世界和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的活动中,取得了一个胜利又一个胜利,共产党国家还未从苏联赫鲁晓夫突然下台(这映证了中国很久以前的一个预言)的震荡中恢复,倾向中国的党派不断增加。原子弹爆炸和早先周恩来总理在非洲的成功巡回访问,都似乎在显示中国就要把亚非国家联合成一个军事集团,这个集团在北京的领导下,要与美国和苏联对抗。
忽然一下,天塌了下来,1965年接下来见证了一系列的倒退,阿尔及利亚Ben Bella倒台,第二届亚非大会的失败,周恩来后来的不成功的访问,以及非洲领导人对发动革命的反感,印巴战争中中国的错误干涉,印度尼西亚亲共力量的失利,以及与古巴的分歧。在共产主义事业中,中国共产党出于守势,而苏联在新的领导人表现出比赫鲁晓夫更明智的举措之后,争取回来失去的阵地和失去的盟友。
关于这些失利,有很多理由,包括美国在越南打下去的决心(这至少显示美国并不一定是北京宣称的纸老虎),和莫斯科更加熟练的战术。某种程度上,也要把中国在亚非地区的太直接了当的方法考虑进去,比如,周恩来经常被重复的说法,“非洲的革命形势已经成熟”,这句话甚至让肯尼亚的老革命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都觉得不安。中国的损失,部分来自于他们缺乏外部世界的经验,除了周恩来和陈毅,最高领导人中几乎无人到过比莫斯科更远的地方,还有部分原因是海外外交官其他工作人员的错误报告。中国人在海外过着孤立的生活,很少离开他们的住处。值得怀疑的是,来自外国的中国外交官的报告,可能在模仿前朝钦差大臣和其他地方官员的的先例,他们总是只说天子想听的,而不是实际发生的,害怕引来龙颜震怒。
但是,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失利似乎还与中国传统的对外部世界的观念有关联,中国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与外人合作的框架。历史上,他们只知道一种外交关系:向北京进贡的臣属国,他们习惯于一次只与一个国家打交道;即使在今天,除了国庆节,中国官员参加外交聚会的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则是,他们只参加没有第三国人员到场的聚会,如果某位外交官打破了这个常规,他会发现他的中国客人闷闷不乐,以后也几乎不会再接受他的邀请了。
中国人不习惯于有来有往的合作外交,他们最高兴的似乎是类似于西哈努克亲王那样的符合传统模式的国家首相。当他们救世主式的共产主义争取主宰亚非和共产党领土的时候,他们不愿意折衷他们的好战教条,也不能接受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一心想把任何联盟变成接受北京领导的君臣关系。
与苏联的关系肯定也是如此,在他们28年的权力争斗中,中国共产党从俄国人那收到的帮助微乎其微。更关键的是,他们经常发现自己的利益被斯大林出卖以达到苏联外交政策的目的。刚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在1949-1950年期间把自己的命运与苏联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从经济需要出发并考虑到大多数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敌意,他们那时没什么其它选择。
有意义的是,这是历史上中国政府第一次选择这样的联盟,随后的事件并没有给中国人太多理由,来证明这个实验的合理性。从一开始苏联方面的经济军事援助的条件就很苛刻,当中国被迫加入朝鲜战争(当联合国军向鸭绿江逼近,威胁到中国国家利益的时候),苏联仅提供了要价昂贵的武器和装备,1958年的离岸群岛(Offshore Islands,是指金门马祖吗?)危机中,苏联也只提供无足轻重的支持。赫鲁晓夫在美国戴维营与艾森豪维尔的会谈中的表现,在中国人眼里是严重背叛了中苏联盟。最后在1960年,苏联突然切断了经济援助,撤回专家,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打击。
这个经历,让中国人不再对盟友存如何幻想。进一步地,因为他们的中央之国的世界观,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肯定对在一个基本上是源于欧洲的蛮夷运动中处于从属地位感到不自在。早在1920年代后期,毛泽东就很洒脱地不顾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和莫斯科的指示,坚持中国革命必须以农民为基础,而不是城市无产阶级。1949-51年期间,其他中国领导人宣称毛泽东发展了马列思想宝库,中国革命而不是苏联,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真正模式。
今天,这种中央帝国世界观的心态,存在于中国在共产主义世界和亚非世界每一个激进战略的背后。 一方面,,中国领导人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的革命,没有什么外来帮助,他们衷心相信毛泽东思想丰富了马列主义,为世界提供了一种不可避免的革命模式;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怀有民族主义抱负的中国人,具有传统的文化和民族优越感,和重振中央帝国雄风的决心,让世界感受中国的威力。在与苏联的论战中,中国一直遣责“大国沙文主义”,同时也表达了对平等互利原则的殷切期望。但是,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从中国强硬外交的失措中看到好战的共产主义与传统的种族傲慢的双重危险。
尽管如此,要重提“黄祸”的恐惧是愚蠢的,要象某些西方领导人那样谈论中国的霸权野心也是可笑的。这类观点仅仅是中国谩骂“美帝国主义”的翻版而已。对于西方来说,重要的是对当前北京的举措中区分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成份,还要研究共产党在实际中作的,与他们发出的威胁进行对比。比如,当中国宣布世界革命的产生,以及农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包围城市(西欧和北美)的时候,这并不是中国侵略或扩张的蓝图,虽然中国确实支持那些地区人民的革命运动。相反,这是以儒教传统来表达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无论在实践中是否可行,目的是影响其他人。另一方面,当中国宣布,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他们对基本的一个民族主义的目标,在这一点上他们绝不妥协。
关键是,要区分中国人所说的(非常强硬)和他们实际所作的(一般都很警慎)。1949年以来,中国人并不是特别激进或具扩张性。当他们使用武力(比如在朝鲜,西藏和台湾)的时候,都是在界定很清晰的范围之内,而且仅仅是当他们感到他们的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的时候。中国人非常清楚他们自己的利益,这可以从他们一直以来对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香港(他们从香港赚取大量的外汇)的容忍中看出来,也可以从他们与非共产党的巴基斯坦,柬埔寨或缅甸的友好关系中看出来。他们也非常清楚他们的经济和军事能力都是有限的。他们也许在远境的外交关系上走了错着,但是至少在边境周边,中国在使用武力上是很现实和克制的。
如果说冷战思维已经过时的话,同样关键的是应该摈弃任何不现实的,对过去的中国的感情上的牵挂。美国领导人似乎尤其总是用共产党阴谋的角度来评价中国,说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压迫那些可爱的人民,人民的基本观念还是反对共产党的传统儒家的孝悌,家庭责任和保守等特质。从某种非常真实的意义来说,官方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恰恰是中国所持有的“我们热爱伟大的美国人民,我们反对狭隘的美国统治阶级”这样一种心态的反面。假如对美国人来说,这种说法有点奇怪的话,中国人也会对林登约翰逊1964年的一个讲话里所谓“我们的老朋友,那些中国大陆上的智慧勇敢的中国人民”感到不可思议。
【访问上海】
就在英制勋爵飞机从云层中下降的时候,空姐在告诉我们扣上安全带后,开始了一段长长的宣讲。“我们现在开始接近上海。这是帝国主义最早压迫中国人民的地方。。。。”
后来我的一位很热心的翻译给我指点那个公园,就是号称挂有臭名昭著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招牌的公园(一些老人坚持说真正的牌子上的文字并没有那么显白)。翻译还很肯定地说,解放前,没有中国妇女敢于在夜里到外滩散步,因为害怕被喝醉的美国水兵强奸。
(上海)变化最明显的莫过于宽敞的外滩上四层楼高的世界最长的酒吧里的吧台。曾经是上海超级私密的上海俱乐部,银行家,外交家和其他东方精英聚会的最佳地点。今天,吧台(100英尺长)还完好无损,但是帝国主义分子已经被赶走了,这幢建筑现在是中外海员交际处。
革命早期,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有一种强烈的浪漫主义特征,表现在他们遵循一种激进的言辞和简单的生活的教理。他们开始的态度是自由主义,甚至可以说是波西米亚式的,1919年毛泽东的一篇批判包办婚姻的文章中,他向“自由恋爱的浪潮”致敬;1927年,毛泽东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描述他老家农民的习惯时写道:“他们也享受相当大的性自由,在贫农中,三角恋和多重关系几乎是普遍现象。”但是今天这些段落都被从毛泽东选集中删去了。中国领导人现在不是鼓励性自由,而是命令压制和净化这种冲动。
【妇女】
那些穿着毫无体型可言的妇女似乎是奥威尔小说中反性联盟的成员,否则还能怎么解释对她们可爱的,漆黑乌亮的头发的毁伤?要么剪成最简单的短发,或者收在从宽松的帽子里搭下来的马尾辫里。妇女穿着跟男人一样,走路也象男人,有时你只能从马尾辫上分辨男女。一位亚洲来访的贵宾对此感到震惊,不禁问道:“你们对妇女的乳房干了什么,把它们都剪掉了吗?”当然,这样说不公平,因为中国女孩子的哺乳器官的发育本来就不显著。很多外国人关于中国女性的概念来自古代画卷上的柔软的美人,京剧中服饰艳丽的女英雄,或是香港新加坡套在丝绸衣服中的吧女,这种观念即是浪漫的,也是不现实的。
在长春,中国的第二大电影制片厂,我遇到了中国的影星,她名叫金迪,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微笑,却穿着松松垮垮的罩衫长裤,看去和其她中国姑娘一样。远不像西方影星的那种奢侈夸张的生活方式,她刚刚从一个很贫困的农存生活了六个月回来。我向她描述了西方影星,比如伊利萨白泰勒,出去会被粉丝包围,金迪漂亮的脸上带着一丝厌恶的表情听着。。。。
【在北京大学宿舍里,作者采访6个男孩女孩】
我说,在西方本科大学生在约会上花很多时间,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他们说他们知道约会,一位最安静也最严肃的男孩说,实际上,如果他们想约会的话,他们可以约会。
“约会的两人会被别人嘲笑或被处罚吗?”
他很肯定地答道:“不会!”
但是其他人说的有点不同,另一名男孩说:“我们不约会是因为我们要节约我们的精力。首先我们要有知识,然后毕业了为人民服务。”
一位表情严峻,带着眼镜的女孩说:“我们住在这里象兄弟姐妹一样。”
年轻的大学行政主任有点坐不住了,他发现我得到的印象并不全是正面的。他对最漂亮的那位女孩说:“再怎么说,我敢肯定你有一个秘密情人。”
她睁着一双美丽的黑眼睛惊叹道:“噢!”边说边晃着一条发黑如丝的马尾辫,她看上去吓着了,可是接着又咯咯地笑起来,但是什么也没说。这也许是真的,但她没承认。
官方对约会持怀疑态度,因为这会让年轻的同志偏离无产阶级道路。
【结婚】不鼓励贵重礼物,北京电台带着赞赏的语调广播了一个故事,说的是河南某妇女民兵营女民兵谭勘文的婚礼,勘文不要任何贵重的礼品,她只要“毛泽东选集和一个痰盂,再要一枝木制步枪。”
中国的意识形态不能融通马克思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所以也就很少承认低调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控制人口增长。在有一千万人口的上海市,一个年轻官员向我保证,中国实践上并没有人口过剩。她的人口密度比英国和很多其它西方国家要小很多,而且在西北部地区,有很大的原始地带可以容纳百万人口。他说:“我们鼓励人口控制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告诉他们,两个孩子是最理想的,再多就会影响母亲的健康。”其他官员否认中国进口粮食--每年六百万吨以上,因为人口增长的需要超过了国内粮食供应。官员们说,对于中国来说,进口小麦,出口大米更划算,因为大米比小麦贵将近一倍,而且,进口了小麦,人民公社就可以将更多的土地用于种植棉花,这是他们最赚钱的作物。
【欢迎外国领导人(苏丹的伊布拉罕阿布德)】我们到达机场的时候,时间还早,这是一个新的,米黄色建筑,庞大而又空旷,跟西方机场那种通常的拥挤和吵闹相比显得没有生命力。
中国领导人出现了,我几乎伸手就可以碰到随便哪一位,我对安全措施的缺乏感到震惊,尤其是与西方保护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的那种横扫一切的举动。我的第一印象是中国领导人不怕暗杀,敢于无所畏惧地在他们的人民中来去。如今我还是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真的,而在那时我很快就意识到,防范措施其实是存在的,不久我就看到了陪伴领导人的便衣警察(不管怎么样,警察总是看上去像警察,无论在哪个国家)。与礼宾官员一样,这些警卫人员熟悉每一个在北京的外国人的面孔,所以很容易发现不善来者(虽然有一次我们把一个好奇的瑞士游客偷偷带入机场的记者区,他距周恩来和柯西金总理只有一口痰的距离)。在阿布德将军沿着外交官的行列走下去的时候,我注视着站在一起的中国领导人,刘少奇直直地站着,僵硬,面无笑容,很镇定的形象,与他的名声很一致,严厉,没有伸缩性的意识形态主义者;周恩来则显得生动得多了:他的浓眉下的表情不断变化,他的目光射向四方,我看到他的脚在跟着乐队点着拍子。
这套仪式几乎从来不变,只有偶尔的某位来访总统或总理受到比全套礼仪要少的欢迎,缩水的欢迎仪式,总是意味着某种政治上的区别,有经验的北京观察家们学会了通过在林荫大道上欢迎队伍的长度和第一次国宴上菜的盘数来预测政治气候。在中国媒体上公开出现攻击持中立态度的老挝首相Souvana Phouma亲王之前很久,就有迹象北京方面已经不再支持他了,当他在1963年初访问北京时,通往机场的道路上没有欢迎人群,当晚宴会上只有五道菜,还没有鱼翅汤。
任何领导人,除非是超人,都不可能没有一点虚荣心,所以面对这种盛大的欢迎仪式,都不会无动于衷。当他从机场出来,就在将要转上宽敞的林荫大道的时候,他看到的第一个景象是他自己画像的巨型牌子,约莫30英尺高,而且总是画得很象。再过去5英里,欢迎群众的喊叫声还未消失,当他的车拐进国宾馆的车道的时候,他注意到的最后一件事是另一个画像,甚至比第一个还大。毫无疑问,他会看到当天北京的报纸,每一份的第一页,左上角都有他的照片,还有社论用夸张的语言大唱他的赞歌。除了个人虚荣心之外,对于任何领导人来说,在世界上最大国家的首都被如此大规模的欢迎,受毛泽东接见,不断被告知亿万中国人民是他的坚强后盾,可不是件小事。对于某些非洲小国的领导人来说,尤其如此。这些领导人可能之前在白宫或白金汉宫受到过敷衍了事的欢迎。事实上,很多亚洲非洲领导人私下很真诚地说过,他们以往从来没有如此深深地被感动和感激过。很多人还坦率承认,他们希望自己国家的人民也能具有这样的训练和纪律。
从实用角度来说,一个来自美国或苏联的大型援助项目抵得上成百个这样的欢迎仪式,尤其是,中国无法提供可与之匹敌的项目,即使是中国提供的小型援助项目,也经常出现困难或者不能按时交货。他们也知道,中国所宣称的所谓后盾,往往只是袖手旁观。亚非国家中关于中国支持颠覆活动的反感也在增加。尽管受到热烈欢迎,每一位民族主义的领导人都知道北京打算以本地的共产党来推翻他的政权。但是,诸如此类的想法都被北京机场跑道上的欢迎仪式扫到角落里去了,低估北京方面娴熟地操纵百万民众对来访领导人所施加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上的得分,是很不明智的。 到了后来,共产党政府的群众掌控技巧更加完善之后,他们把人民的海洋整编成我所见过的最惊人的游行。
一次游行之后,两名西德记者就他们的观感争了起来,每个人都承认有一种特别的感受,都联想到希特勒在纽伦堡的集会。其中一人痛恨所以的集权体制,他说他对这样巨大规模的活动感到害怕和厌恶,另一人对中国比较同情,说这与希特勒的游行示威没有可比性,因为北京的游行更加放松,更少暴力倾向,还有女性参加,似乎并未显示特殊的民间神秘色彩的感情暴发。只有一个习惯于最严格和经常的管控的民族才能完成这样的技艺,我相信,这一点是从这种令人难以置信,印象深刻的游行中得出的主要结论。
从巴黎到雅加达,我看过很多情绪激动又愤怒的暴乱,相比之下,北京的抗议活动虽然也是大规模的,还有军事化倾向,但是实际上并不比一次周日教会学校的野餐更加过火,我发现示威者们很放松,没有脾气。对大多数人来说,喊口号,挥拳头只是他们早就习惯的一个例行活动,大多数人是青年人,我怀疑他们对能逃离日复一日单调沉闷的常规而到室外呼吸新鲜空气感到高兴。
中国人有一种相当成熟的公关意识。他们知道他们的抗议示威活动虽然不能给居住北京,对此早已习惯的外国人有什么触动,但是却能在世界上占到头条新闻。最主要的,他们给人一个印象,中国在危机中积极活动,因此他们印证了中国已侪身大国行列的宣言,他们要在每一个重要对抗中让人听到并注意他们的声音。当然,这些抗议活动往往不过是中国试图掩盖其对最终结果无能为力的掩饰。这些抗议活动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们越来越不吸引人,就象喊“狼来了!”的男孩一样,相信的人越来越少。尽管如此,我怀疑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这些抗议示威,以及所有其它的大型群众活动,都在国内政治上有重要意义。他们最喜欢的一个技巧是制造一种战斗氛围,以此用不断的鼓动来训练他们的人民,在这一点上,他们遵守其它极权国家的模式。不管这些大型集会游行对外部世界的效果如何,它们能鼓动国内人民,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导到政府的目标上,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转移他们对日常生活中的困难的抱怨。
【下面的照片,来自另一本书:《China Hands: the Globe and Mail in Peking》,泰勒是该书的编者,书里写了历届环球邮报驻京记者的记录,1984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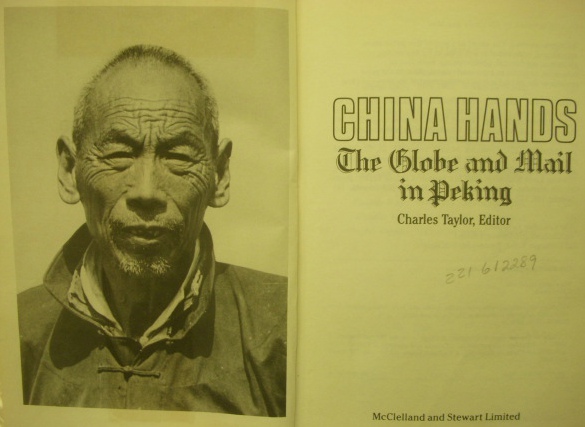
书名页。

难民进入香港前,等待面试。

这是查理斯泰勒,从Shumchum过境进入中国,所谓Shumchum,应该就是深圳,60年代只是一个村庄的规模。

红卫兵在苏联大使馆门上挂苏联领导人的纸象。

上,北京市民在故宫附近读大字报,下是北京的游行示威

1960年代,中国和英国发生过外交纠纷,中国使领馆人员与英国警察发生冲突,有中方人员被拘留,于是中方采取报复行动,除了人民“自发”游行示威,抗议英国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外,中国方面软禁了英国驻京记者Anthony Grey,这是Grey在其北京住处门外。Grey后来写过一本书,我前面的博文曾提及。有意思的一位衣着老式的中国老人柱着拐杖,创入镜头。

这是比较和平的景象,邓小平和李先念,时间是1970年代邓小平复出后,看样子应该是在机场等待欢迎外国领导人。

不用多解释,周恩来总理欢迎你克松总统,后来是应该王海容,不象唐闻生。

比较生活化的镜头,加拿大激进保守党(Progressive Conservative Party)领导Robert
Stanfield访问中国时在定制一件中山装(Mao's suit),两口子似乎都挺大年纪了,太太背有点驼了。

又是一张有意思,不过是政治意思的照片,左起,康生,原图英文说他是中国的贝利亚(还有人记得贝利亚吗?苏联的希姆莱,斯大林的打手,屠夫),周恩来,陈伯达,姚文元(英文说他是毛泽东的女婿son-in-law,显然搞错了。1970年代中国有很多小道消息,但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

华主席,汪东兴,这应该是1976,1977年前后的照片。

英文说是军人在天安门广场准备参加毛泽东的葬礼。但是为什么都没戴黑臂套呢?另外,正对镜头的女战士,看着象是在微笑。
书中环球邮报驻京记者名单:
Frederick Nassol,1959-1962
Charles Taylor, 1962-1965
David Oancia, 1965-1968
Colin McCullough, 1968-1969
Norman Webster,1969-1971
John Burns, 1971-1975
Ross H. Munro, 1975-1977
John Fraser, 1977-1979
Bryan Johnson, 1979-1981
Stanley Oziewicz, 1981-1983
AllenAbel,1983 -书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