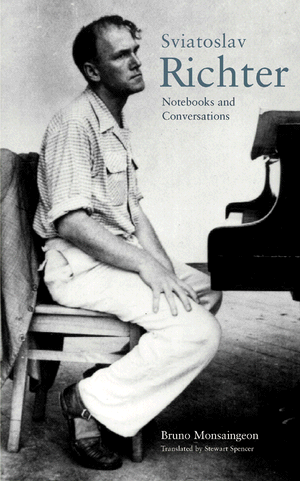
Sviatoslav Richter - Documentary - The Enigma - vol. 1
里赫特——谜的剧情简介 · · · · · ·
纪录片拍摄得非常朴实,传主本人对着镜头,用俄语讲述他的一生事件和艺术观念。态度和用语相当直率,据说在书中,保留了更多他的“粗话”。(豆瓣)
导演: Bruno Monsaingeon / 布鲁诺·蒙桑容
主演: 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
制片国家/地区: 法国
语言: 俄语
上映日期: 1998
李赫特 - 迷 Sviatoslav Richter - The Enigma
李赫特,他自成一个世界,隐秘而耀眼。他如深海鱼,盲目但闪烁光华。他是无可争议的钢琴大师。
他喜欢电影,但讨厌摄像机。他不喜欢分析、谈论或袒露自己,他对时事、政治、赞誉和尘世漠不关心,当权者的变幻或音乐界的成规都无法影响他对至纯至高境界的狂热追求。只有音乐才能让他投入,乃至奉献一生。
他不是为效果而演奏,挥洒间不留斧劈凿痕,他朴素地演奏……他全然自由……
(布鲁诺·蒙桑容 法国电视导演、采访人)
开场白
我记忆力惊人,好到无法忍受。我去过不少城市,在那里遇见过五十来人,他们的名字全留在我脑子里,我都记得,这简直是折磨!还有我的所有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每当我开始旅行,就会受到这种折磨,无论在俄国还是西方,都一样!
但我却记不清数字,连我的地址也记不住。除了在奥德萨,涅任斯卡亚大街二号十五单元(李赫特在奥德萨的住址)。还有那些姐妹们:
亚丽桑德拉·瓦西利耶夫娜和奥尔嘉·瓦西利耶夫娜、柳德米拉·瓦西利耶夫娜、叶莲娜·瓦西利耶夫娜、安娜·瓦西利耶夫娜、卡杰琳娜·瓦西利耶夫娜和维拉·瓦西利耶夫娜,我全记得!
一九三一年,那年我十六岁。父亲把我介绍给他的老朋友们,还有他的女性崇拜者,八位谢苗诺娃姐妹。她们住在带廊柱的宅子里,和屠格涅夫小说里的一样,她们全上了年纪,都很老派,彼此相互闹个不停。但她们为人非常好,她们是我的第一批听众,在她们那里我首尝听众捧场成功的滋味。她们都是……我该怎么说?怪怪的老好人!每个人都是,她们姐妹八个都是! 我在她们宅子里举行家庭音乐会,我演奏了舒曼的协奏曲,单钢琴版的,非常成功!那时我就下定决心 - 要做一个钢琴家。我发觉自己也拥有了女性崇拜者,一下子八个!
所有这些回忆,也许很有意思,但对我而言,已没有滋味,我几乎讨厌它们!要知道,我已经八十岁了!
父母和童年
我一九一五年生于日托米尔,在乌克兰。那时还不这么叫,当时称为"小俄罗斯"。我父亲也生在那里,虽然他是德裔。他住在那里直到服役期。他后来去维也纳学钢琴和作曲, 在那里交了不少出色的朋友,一些很出名的德国作曲家,例如弗朗茨·施莱柯尔。
学业结束后,他举行了音乐会并在维也纳整整生活了二十二年,但他每年总回日托米尔消夏,他和母亲就是在那里见面的,她成了父亲的学生。
母亲的娘家姓是莫斯克廖娃。她是俄罗斯人,父亲是地主,他一直不同意女儿的婚姻,因为我父亲是平民!但我父亲还是娶了母亲。
我父亲是个很棒的钢琴家,奥德萨音乐学院请他去任教。可我染上了斑疹伤寒,没法去奥德萨。母亲不得不离开我,去找我父亲 他也得了伤寒。她不得不滞留在那里,再加上白军、红军……等到她来接我,已经是四年以后了。这些年我一直和玛丽姨妈住。后来我母亲来接我,从奥德萨到日托米尔,路上整整用了一星期!那时的确世事艰难。
我的母亲是个无以伦比的女人,很实际,有时实际得过份!这导致我对所有实际事务都很反感。她总是骂我,说我对周围的事不闻不问,我那时的确如此。
一切都很美好,直到我十一岁,然后就是我一生中最糟的时期:上学。我恨学校,我们校长严厉得可怕,她叫彼得斯太太。我们都吓坏了,其实她长得很可爱,像蒙娜丽莎。她尽管对我有好感,但还是会对我叫喊,用德语喊更吓人:"你们这些懒骨头!特别是李赫特,简直懒得发臭!"
自学成才
在八岁的时候,我试着把手放到琴键上。我父亲看到我乱弹时吓坏了,但母亲对他说:"让他一个人弹去。他不愿意弹音阶就算了。"
就这样,我从没弹过音阶,也没弹过练习曲,从来没有!我从肖邦第一首夜曲开始入门,接着是《e小调练习曲》(作品二十五之四)
我只弹我感兴趣的,像《唐豪塞》、《罗恩格林》……边弹边改编!我还作曲,当时最吸引我的是剧院,《阿伊达》、《弄臣》都让我兴趣盎然,而钢琴反倒其次。
我十五岁时,有机会成为钢琴伴奏,在很多俱乐部参加小型音乐会。通常我被送到那里,晚上在城外,我就在舞台上当场弹奏,为歌手伴奏,还有小提琴、杂耍等等,全部是即兴发挥!于是在十五岁上,我就开始挣点钱。有时他们不付钱,就给我一袋土豆。那刚好在集体化以后,日子很苦。我早在十四岁时就在海员俱乐部演奏,业余歌手在那里唱一些歌剧片断,用钢琴伴奏,我这样乾了三年。这些业余歌手水准差得吓人,但我毕竟长了不少经验。后来歌剧院也听说了我,就喊我去给芭蕾伴奏,看歌剧让我获益非浅。 首席指挥斯托尔曼,一个很诚恳的职业音乐家,也许技艺并非一流,但仍然值得尊敬。他杀了自己的妻子!因为她毁了他所有的作曲手稿。他等妻子睡着时开枪打死了她,可后来却被宣告无罪。一个漂亮的妻子,她把所有手稿都烧了,纯粹出于嫉妒。
奥德萨歌剧院的曲目在当时很前卫,有普契尼的《图兰多公主》,克任纳克的歌剧《容尼奏乐》,一个很棒的剧院。他们许诺说以后让我来指挥,我最想指挥的是格拉祖诺夫的《蕾蒙达》,可他们却把职位给了别人,一个平庸的家伙。
我父亲被正式邀请,为德国领事的孩子上课。有时我也被邀请去领馆,我在一些特殊场合演奏过。例如,当兴登堡逝世时,我演奏了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奏鸣曲二十六号的第二乐章),还有《诸神的黄昏》(应是其中的《齐格弗里德的葬礼》)。
在十九岁时,我突然有个荒唐的念头,想开场独奏音乐会。我几乎浏览所有的钢琴文献,一场肖邦独奏音乐会如期举行。地点是奥德萨的工程师俱乐部,场子很小,观众都是朋友。《第四叙事曲》弹得不错,《第四练习曲》(作品十号之四)作为加演也过得去。我的音乐会并没产生什么影响。
背井离乡
奥德萨很特别,虽然有些动荡不安,但它仍然迷人。可是在一九三三年,奥德萨所有的教堂都被毁了。他们扯下教堂的钟,推倒了钟楼,在教堂原址上盖起学校,又脏又乏味!整个俄罗斯都是如此!
在三五年和三六年,如果有人拉响门铃,特别是在晚上,我们会被吓死!我还记得一个很傻的梦 - 门铃响了,我去开门,"是谁?"在门后我听到一个发狂般的声音:"别开门,我是强盗!"我醒了,满身是汗,对门铃声怕得要命。
那时很多人被抓了,在歌剧院,情况很可怕。人们被隔离,每个人都要谴责所谓的"人民公敌",任何人都可能被指控!后来,我想:够了,再也没法忍受了!他们来威胁我,要送我去当兵。所以我决定去莫斯科,去找涅高兹。
涅高兹
我一生中有三位老师,涅高兹、父亲和瓦格纳。我很喜欢涅高兹的演奏,还有他的为人。我下了决心,进入莫斯科音乐学院,师从涅高兹。我喜欢他还有其它原因,他就像是我的父亲,更让我放松。我弹给他听,亮出我的看家曲目,肖邦《第四叙事曲》。然后我们聊起了瓦格纳,我给他的印象不错。
(涅高兹的回忆:"人们叫我去听一位年轻人的演奏,他想进音乐学院,我问:'他读过预科班吗?' '没有 他是野路子!' 一个没受过正规教育的孩子,居然想进音乐学院!我对这家伙很好奇。 一个非常深沉年轻人来了,坐下来演奏贝多芬和肖邦,还有他自己的作品。我对我的学生低声说:"这人是个大天才!"斯维托斯拉夫·李赫特当天就成为了我的学生)
我被接纳了,但有条件,要我学习所有科目,可我不乾!光在头一年里,我就有两次被赶出来!
涅高兹对我就像慈父,他总是在强调:音色。他解放了我的演奏,我的声音得以运用自如,它至今仍具有力度。这也得益于我在歌剧院弹伴奏。
在李斯特奏鸣曲中,他传授我个中精义:静默以及如何弹静默的艺术。
我搞了一个小花招:上台,坐下,一动不动。在静默中,暗数到三十,然后再弹出G音。这能在观众中制造近乎惊恐的效果:"发生什么事了?"当然,这很戏剧化,是音乐的戏剧,惊诧就是其精义所在。有很多大钢琴家,他们给你的菜谱,你老早就烂熟了,只有出人意料才会留下深刻印象。
我第四次给他演奏李斯特奏鸣曲,当着全班的面。他听后说:"我已经无话可讲了!"
他从没出国,他们不准他出去。他也很少演奏。有一天,他开了一场舒曼作品音乐会。开场曲目他弹得像头蠢猪,每个小节都有错音!然后是《克莱斯勒偶记》,一个奇迹!接着是《幻想曲》,我们再也没听过如此神奇的演奏。
教学是件可怕的事,对钢琴家来说是致命的,而他却全身心投入教学。他的音色出神入化,我依他的路子演奏,把握精义。有一次我弹德彪西给他听,他说:"你的德彪西让我听得入迷。"
我住在涅高兹家。一天晚上,我弹了整出《特里斯坦》,在结尾时,古萨科夫 - 他也是个学生 - 孩子气地说:"每个人都跪下来,向斯拉瓦(斯维托斯拉夫的爱称)致敬!"我当然反对,说:"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不如向我吐口水,请向我脸上吐!" 古萨科夫是个瓦格纳迷,几乎迷得发疯!
在四一年十二月,我举行首次公演,曲目是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我就如此开创事业。
战争
我的职业生涯随着战争起步,那时到处都邀请我去,莫斯科、基辅、高加索……
在四三年、我赴阿罕格尔斯克演出,还有摩尔曼斯克。那里到处是猛烈的炮击,那些城市几乎变成废墟。我记得有一天特别冷,下雨,而且阴沉。大街上在放广播,是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奥伊斯特拉赫演奏。拉得很好,带着忧伤的调子。
要论轰炸,哪儿也比不上地狱般的列宁格勒,相比之下,在莫斯科还可以勉强过活。我首次到列宁格勒演出是在四四年一月五日。我是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到的,就我一个人。我从窗口望出去,听着隆隆炮声,能看见圣伊萨克大教堂,我就这样过的新年。到处一片惨淡,有种神秘的美。
在演出之后,我留在城区。他们检查了我的身份证后说:"你不能留下! 你是德国人!"而德国人却说:"你是俄国人!"
我在爱乐大厅举行了音乐会,所有窗户都是破的,是早晨的炮击震的。听众都裹着大衣,对音乐会我感觉不错,在演奏时我没觉得冷!
家庭悲剧
(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爆发,李赫特的父亲因是德裔,又在德领馆授课,被指认为德国间谍,被处决。后证明是冤案,得以平反。)
在俄国,样样事情都堵着瞒着,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比如我父亲,从没人提过我父亲被枪决的事。他的确是被处决的,就在德国人打到奥德萨之前,我对此一无所知,因为战争期间,我都呆在莫斯科。我母亲再嫁,逃到德国去了。她的第二个丈夫,曾更名改姓,有人以为他是我父亲的兄弟,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一章。
康德拉季耶夫,我母亲的第二个丈夫,他是一个高官的公子,其父在旧俄政权任职。他也是德裔,改过姓,所以能避过革命。他从莫斯科逃到奥德萨,隐名埋姓。在奥德萨音乐学院,他还是感到不安全,怕有朝一日被揭发,所以他总是在改名字。他有好几年卧床不起,假称自己有肺结核病,直到德国人来时他才起来。他一直装病,装了二十年。母亲一直照料他,无微不至。我父亲全知道。当战争开始时,他搬来和我家人一起住。他们要我父母疏散,就单单我父母。要出发时,我母亲却拒绝离开,因为她不能把病人丢下不管!我父亲被处决后,我母亲和他在一九四一年离开俄国,和其它德裔人迁居到德国。在那里,他改姓李赫特。他对外称是我父亲,你们能理解,我很生气。当我到一些德国城市,人们告诉我:"我们见过你父亲!"我后来去德国拜访他们。
那时我母亲快死了,她住在医院里。
我在维也纳的首演音乐会真是可怕!我当时状态不佳,是从意大利过去的,在音乐会的前一天刚到。就在音乐会当天,我继父来见我,照直就说:"我的妻子去世了!"我后来再也没在维也纳演奏过,那场音乐会是个灾难,乐评极其恶劣,标题是《传奇的破灭!》!我那次弹得真是糟没法讲!
普罗柯菲耶夫
一九四一年三月份我演奏了普罗柯菲耶夫的《第五钢琴协奏曲》,作曲家亲自指挥。当时战争还没爆发。
我曾演出过他的《第六奏鸣曲》,他出席了那次音乐会。他当时问我,是否愿意演出他的《第五协奏曲》。他说:"作品还没有获得成功,不过如果你愿意演奏,或许它会受欢迎。"他当然在开玩笑,两个月后,我公演了这部作品,这是值得纪念的时刻,听众对演出反响极佳!连普罗柯菲耶夫对此也万分意外,他对我说:"我晓得了-他们希望你加演肖邦《夜曲》!"
普罗柯菲耶夫很有意思,但也很危险! 他会对你玩花招,生性冷酷而又生气勃勃。他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只要有委约,他就写。比方说《您好!》,这部作品至今还无法演奏。它是为祝贺斯大林的生日而作,的确是部天才之作,一座丰碑,但却是纪念普罗柯菲耶夫才华的丰碑。
后来就是我的首场独奏音乐会,在一九四二年夏天。我演奏普罗柯菲耶夫的作品,还有六首拉赫玛尼诺夫的前奏曲。普罗柯菲耶夫讨厌拉赫玛尼诺夫,对拉氏的作品他老是口出不逊。为什么?因为他受拉赫玛尼诺夫影响很多!普罗柯菲耶夫的钢琴作品风格是得自于拉赫玛尼诺夫,比方说后者的《音画练习曲》,但这部作品却是普罗柯菲耶夫最讨厌的!
说真的,有时候我挺冒险的。比方说,学普罗柯菲耶夫的《第七奏鸣曲》。我只用四天,全部背谱! 这首奏鸣曲非常动人。
普罗柯菲耶夫有位好友,钢琴家马克西米连·施密多夫。他把《第二奏鸣曲》题献给他,还有《第四奏鸣曲》,都是追念,还有《第二协奏曲》,也是追念。施密多夫曾给他写了封信:"谢廖沙,有件事告诉你 - 我自杀了!"人们在两个月后,才在树林里找到他的尸体。
在四三年,他写了《第七奏鸣曲》由我首演。《第八奏鸣曲》题献给吉列尔斯,他演奏得很辉煌。普罗柯菲耶夫死前不久,曾对我说:"我给你写了一首奏鸣曲。"就是《第九奏鸣曲》。
在一九四八年,他们发布了那个愚不可及的决议,压制新音乐和普罗柯菲耶夫。尼娜和我不管它,音乐会照开不误,其中有里姆斯基和普罗柯菲耶夫的作品。我们就这么乾了,他们也许没看到海报!
尼娜
我们首次见面很有趣。
在我刚进音乐学院不久,一位单簧管乐手去世了。在葬礼上,很多人都去演奏了,有涅高兹,伊古穆诺夫等人。还有一位歌手,我被她震住了,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尼娜·多莉雅奇。
尼娜非常可爱,一位真正的公主。很多葬礼都请她去唱,她说:"我成了葬礼歌手。"
阿诺索夫,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父亲,他对我说:"你该和她同台演出。"
(尼娜的回忆:"他到爱乐乐团来找我,说:'我想和你开音乐会'。他当时已经很出名了,似乎不太可能为我伴奏。我回答:"你是想和我合开音乐会吗?"他说:'不,我想为你伴奏!'")
一九四六年,我住进了尼娜的公寓。在此之前,我居无定所,只有两个小间,是公共宿舍,和其它人家合住,那是一个三口之家。
(尼娜的回忆:"他总是无忧无虑,以前他睡在涅高兹家的钢琴下面,地方小极了。他对舒适的生活总是很漠然。")
尤金娜
我常在葬礼上演奏,比如卡查洛夫的葬礼,还有尤金娜的葬礼……
我认识她,但不是很熟。对我,她总是多疑而刻薄。"哼! "她提到我总是如此:"就是那个只会弹拉赫玛尼诺夫的家伙!" 她对我评价不高。
她总是给人印象深刻。她弹李斯特棒极了,弹舒伯特最后一首奏鸣曲同样美妙,虽然都和作曲家原意都相去甚远。
她曾在战时演奏巴赫的作品,《降b小调前奏曲》,弹得又快又猛。涅高兹去后台问她:"你乾嘛弹得那么凶?"
"我们不是在打仗吗?"这就是尤金娜的性格!"我们在打仗!"
听过她的音乐会后,我肯定头疼,她总给听众留下强力的印象。她天份极高,是个独立特行、敢说敢做的女人。无论她何时步入舞台,看上去总像是刚从滂沱大雨中冲进来。在演奏前她总划个十字,我不反对这样,可你要知道这是在苏联啊……观众都为此而崇拜她。出于义愤,她在告别系列音乐会上朗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这很可怕:她那时牙都掉光了! 她过得像个流浪汉!
(采访者:"你在她的葬礼上演奏过吗?")
当然!你知道我弹什么? 拉赫玛尼诺夫!
指挥
我会是个不错的指挥,但我生平只指过一次!人人都对这事感到不可思议。我曾打架,弄断了手指,真的!我想:也好,我可以弹拉威尔的《左手协奏曲》了!
接着有场普罗柯菲耶夫的《交响协奏曲》,我很想指挥。但这部作品被官方禁了,文化部处处和普罗柯菲耶夫过不去。我就讹他们:我坚持说手指断了,很严重。这还真管用!
总共只有三场排练,大提琴手们全都是土包子,当听到独奏声部时,他们都在傻笑,独奏者是罗斯特罗波维奇!首演相当不错,连普罗柯菲耶夫也说:"如今我的作品有一个指挥专家了。"我后来再也没乾过指挥,其中有两件事我都不喜欢:分析和权力。没有指挥能逃过这两样东西,可它们不对我胃口!
巴赫
听巴赫永远没错,哪怕仅仅是出于洁癖! 我们总习惯在圣诞节欢聚一堂,聆听巴赫所创作的奇迹 - 《圣诞清唱剧》。第一通定音鼓就能让我兴奋狂喜!
我在第比利斯第一次演奏了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这是一个挑战,又冒险又费劲。我用了一个月来背谱,同时我还要演奏贝多芬的《热情》。在第比利斯,我弹得很糟。但两天后,在巴库,情况就好多了。
但在那里我碰到一个烦心的意外:我发现他们开始对我盯梢。我有次赶不及,就跑着回旅馆。当我回头时,发现一个家伙也跟着我跑。我没有进旅馆,而是拐进了下一个胡同,他还是跟着跑,我就向他冲过去!我们撞到了一块!
我后来一直被盯梢,他们跟了我好几个月。我开始对他们耍花招。有次,在公交车上,有个家伙和我面对面。
我对他说:"下一站你下车吗?"
"是的。"
"那好,我就不下车。"
他只能灰溜溜地下车了。他们到处都跟着我,后来他们撤了。
我能说什么呢?也许是因为巴赫,有一阵子,我到处演奏巴赫的《平均律》。后来我曾收到一封信,上面写:"别再用巴赫来折磨我们了!"
早期巡演
第比利斯之行才是我演奏生涯的真正开端,而不是纽约音乐会,可人们总以为是后者。我从不觉得在俄国和去国外开音乐会有什么区别,美国之行是个例外,在那里我情绪低落,我是被迫去的,我根本不想去美国!还有那么多有意思的地方!我甚至曾在农庄里演奏。我去过西伯利亚,那里每一个新的城市都强烈地吸引我。
(尼娜的回忆:"他习惯到处走走,曾两次步行环游莫斯科。对那里的城郊他了如指掌。他云游四方,坐火车、坐汽车,但他恨飞机。他第一次国外巡回演出是去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人很钟爱他,称他为'布拉格的最爱'。")
有几场音乐会在工厂举行,不太成功,我是从俄国来的嘛! 大厅里到处都挂着红旗,我问他们:"你们是要开党代会吗?"他们很惊讶。
我问:"乾嘛要挂红旗?"
他们说:"可它们是为你挂的呀!"
我说:"可我又不是来开会的!"
在布拉格,我的音乐会很成功。演奏的曲目很杂,例如肖邦的《第二谐谑曲》、拉赫玛尼诺夫等等……
我当时两度出国演出,第三次一直要等到一九五三年。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Auf Wiedersehen! (德语:再见!)
斯大林葬礼
关于我的事有许多胡说八道,都是荒诞不经!说什么我故意在演奏时抗议斯大林……他们说:"我在斯大林的葬礼上演奏。" 没错,我是去演奏了。他们还说:"我选了一首很长的巴赫赋格,听众对我嘘声一片。"什么人敢在斯大林的葬礼上发嘘声?他们蠢得连谎都说不好!还有:"警察把我从钢琴边拉走。" 事实上我是在一架立式琴上演奏,周围都是乐队,那些说法是彻头彻尾的编造!
我当时在第比利斯,从莫斯科来了封电报,命令我坐飞机回去。天气很差,已经没有航班了。他们把我塞进一架飞机,周围全是花圈,就我一个人!
我一抵达,就去演奏。我们头顶就是棺材,远在视线之上,我没法看见。我看见几个大官,谁?像是马林科夫,他看上去吓坏了,我想他大概觉得大难临头了。他是预定接班人。可他后来保住了位子和性命。
钢琴踏瓣坏了,这种情况下,我没法演奏。我垫了本谱子在踏瓣下面,总算可以凑合着用了。我发现有人四面八方向我冲过来,他们以为我在放炸弹!
整个过程都让人不舒服,有件事特别让人反胃,我当然是从音乐的角度来看的。午夜时分,他们要将斯大林的遗体搬走。指挥家梅里克-巴夏耶夫开始指挥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演奏到发展部的时候,在这骨节眼上,一支军乐队打断了他,开始吹肖邦的《葬礼进行曲》,令人讨厌!
当我离开葬仪大厅时,我听到了广播,响彻整个莫斯科:"贝利亚 - 布尔加宁 -马林科夫。" 我并不特别喜欢斯大林,但这些事让我想赶快去冲个澡,我感觉就像个局外人!
Sviatoslav Richter - Documentary - The Enigma - vol. 2
第二部
对俄国的大艺术家们而言,斯大林的去世升起了铁幕,西方世界开始了解他们。像奥伊斯特拉赫、吉列尔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等等。李赫特成为传奇人物,但他要到一九六零才获准到西方演出。当年,他首度赴美巡演,六场卡内基音乐厅独奏音乐会精彩绝伦,其效果不亚于重磅炸弹。同时他的曲目库日渐庞大,几乎囊括所有钢琴文献。
(布鲁诺·蒙桑容 法国电视导演、采访人)
演电影
我曾演过一个小角色,是在影片《作曲家格林卡》里面。我演李斯特,这部电影面面俱到,反映了格林卡所处的时代。里面有普希金、托尔斯泰。影片大获成功!
影片中我根据《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的进行曲主题即兴演奏,格林卡进来时,我刚好结束。这个场景拍得很美妙,很漂亮,很有效果的一段插曲。
赴美演出
我几乎没去成。我甚至想下错车,我就是不想去! 我想有意赶不上火车,这样美国之行就会泡汤。
(李赫特的妻子尼娜:"他对去美国演出毫无热情,尤洛克,美国的演出经理,他每年都要来莫斯科。他老是问起李赫特,他们总是对他说:'李赫特病了,他没法去。' 有一天,我们意外撞见他,尤洛克很惊讶:'你不是好好的吗 健康极了!'"奥伊斯特拉赫与康德拉欣,一直在恳求中央委员会,他们说:'让李赫特去吧! 当我们出国时,他们首先问的总是:李赫特什么时候来? 这让我们很尴尬。'最后他们决定,让李赫特出国演出。这是赫鲁晓夫亲自作的决定。)
我第一次去美国,克格勃给我派了个"贴身保镖"。小伙子看上去很正派,他的老板,是一个在列宁格勒的家伙,指示是:看住,跟着他。有一次,我要去芝加哥的博物馆,在门背后,我发现了这个叫安纳托利的小伙子。他很窘,嘟哝说:"是他派我来的! 是他!"
"你的任务就是演奏!" 他老是对我这么说,我被搞得神经紧张,变得慌慌张张的。
(采访者:"你可是获得了巨大成功!" )
可能吧,但我发挥得很差,真的很差! 弹了大把的错音! 我受之有愧。
(尼娜:"音乐会结束,空前成功!就会有一大群人涌到后台来。但他自己会很不开心,他会说:'瞧,这就叫成功!可我感觉不行,他们什么都不懂,根本没听懂!'")
我不喜欢去见那些名人,但总有那么多的会见。
(尼娜:"和明希合作时他很激动。在排练结束后,斯拉瓦过去吻明希的手。我觉得明希毫不惊诧,他很有风度、很朴素地接受了。对了,还有奥曼迪。他们见了很多次,在一起合作演出。奥曼迪总说:"斯拉瓦,你该留下。你乾嘛要回去,移民吧!" 斯拉瓦对我说:"他们怎么都这样劝我? 可我在家感觉很好!" )
我觉得美国单调划一,到处一模一样,我不喜欢那里。
(尼娜:霍罗维茨邀请他去,他说他们相处得不错。然后是阿图尔·鲁宾斯坦)
(鲁宾斯坦的回忆:"他弹得棒极了! 我特地从欧洲赶过去,那时李赫特已经开了三场音乐会了。我对'伟大的李赫特'非常好奇,就去听他的音乐会。他演奏了三首拉威尔的曲子,不可思议! 声音美得出奇! 我以前从没听到钢琴会弹出这种声音,简直就像另一件乐器。我当场掉了眼泪。李赫特是个音乐巨人,悟性超人,他演奏钢琴,而钢琴也回应他,他和钢琴一起歌唱。")
音乐哲学
学得快其实很容易,难的是要从容不迫,同时还要朴素! 我拿起一页谱子,除非我掌握了,我绝不弹下一页,然后再一页页往下弹。
(尼娜:他对别的钢琴家说:"一天练三小时 绝不要多!" 他们问:"那么你自己呢,斯维托斯拉夫·特奥菲罗维奇?" 他说:"同样,三小时!"但他有时候一天练习十到十二个小时!)
胡说八道! 十二小时? 不可能! 也许有时候当我尽快赶一首曲子,比如,普罗柯菲耶夫的第七奏鸣曲,在最后几天我也许会练得多一点。但平时,不会! 十二小时? 从来没有过!
(古尔德的回忆:我向来认为音乐表演者可分两类:其一努力开发乐器性能,其二反之。第一类诸如音乐史上的传奇人物 - 李斯特、帕格尼尼,-直到后来以魔鬼技巧擅胜的大家。这类音乐家致力发掘他们和乐器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第二类音乐家试图超越演出的魔力,在他们和乐谱之间创造幻景,以此来帮助听者领会音乐精义,听众与其说被演奏者所吸引,不如说更关注音乐。我确信在我们时代,第二类演奏家的典范是斯维托斯拉夫·李赫特。事实上,李赫特所做的是在听者和作曲家之间插入他的强力个性,就像某类连接环,以此他向听者揭示作品,往往给予我们意外的崭新视点。)
舒柏特的《G大调奏鸣曲》是我最钟爱的舒柏特奏鸣曲。我第一次演奏舒柏特的奏鸣曲,老辈份的教授们对我说:"舒柏特? 太让人反胃了! 舒曼就好得多嘛。" 很多人说:"这家伙是疯了吧?" 可我不是为观众而演奏,我只为自己演奏,如果我乐在其中,观众自然也会乐在其中。
我只想演奏伟大的音乐。
演奏会后,古尔德到后台来他说喜欢我的演出,但仅指我个人而言。问我是否愿意交流彼此对舒柏特的见解?
(古尔德:我第一次听他演奏,是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一九五七年五月。他以舒柏特最后一首奏鸣曲开场,《降B大调奏鸣曲》,有史以来最冗长的奏鸣曲之一,而李赫特又以从未有的慢速演奏,使其更为漫长。我愿坦白陈言两件事,其一,也许不太合常理,因为我本人并非舒伯特音乐的表述者,我觉得其音乐中的反复结构棘手费解,我往往在其中精疲力竭。我忍受着这首漫长的舒伯特奏鸣曲。后来发生了什么?一个小时之后,我已陷入一种昏昏欲睡的恍惚状态。我所说的舒伯特的反复结构被遗忘了,我先前认为仅起装饰作用的音乐细节,如今显然成为音乐的组成基础,我至今仍对这些细节记忆犹新。对我而言,这似乎是两种毫不相容事物的合体:用一种自发的即兴来揭示深刻精密的内涵。正像我后来聆听多款李赫特录音时所感受到的那样,我亲身见证了一位无比强大的交流者,他们以音乐铸造我们的时代。)
我在黑暗里演奏,是为了更好地集中精力。听众也能更好地聆听音乐,有什么好看? 演奏家? 他的手吗? 用不着! 他的脸部表情? 乾嘛? 什么都不需要,只表现作品,表达出作品中的音乐。谁会需要看呢?
(采访者:人人都说你只演奏你喜欢的作品? )
没错。
(为什么?)
因为我很自私。
有些人写文章说,我临时取消演出的习惯比我的音乐会更加出名。这些耍笔杆的! 的确,我生病时会取消音乐会,他们就说我反复无常。
不是那么回事!我不是取消,我只是推迟。在巴黎,有过场音乐会,在苏联大使馆举行。那儿有架斯坦威钢琴,调音师去那里检查后说:"这钢琴根本没法演奏。" 于是,我取消了音乐会。大使照常漫不经心,没加注意。音乐会当天下午五点,他打电话来: "观众都到场了,我该怎么办呢? 自杀吗?" 他总算说动了我,于是我去了,也许会很糟。我以勃拉姆斯《第二奏鸣曲》开场,整场音乐会还算过得去,称得上是我当年最好的一场!
在美国,他们让我去挑琴,有整整一打钢琴! 这就是我弹不好的缘故!因为我觉得我从来挑不对钢琴,我挑不来钢琴,从来不会! 挑钢琴就像选择命运,说的容易做的难。为音乐会挑钢琴很有害,会让你士气消沉,我向来把这种事交给调音师。试来试去,根本没用!这应该是调音师的活。就像圣彼得,只要心诚,就能在水上走;如果心不诚,就会沉没。
伊古穆诺夫有次对我说:"你压根儿不热爱钢琴!"
我回答:"也许如此 我更热爱音乐。"我有时在糟得可怕的琴上会弹得很好。
(采访者: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琴? )
我想要的总是没有,关键是在音色。雅马哈有这种音色,就是"极弱" (pianissimo),最微弱的弱音,是最勾人魂的,不是极强,而是极弱。
(尼娜: "他在早期音乐会上弹得很粗糙,加上他当时脾气暴躁,往往就会弹得震天响。后来他逐步开始注意音色,如今他的音色已进入朴素单纯的理想境界,越来越自由。他是花了不少时间,才达到神奇的美声(Bel Canto)。")
有一次,普罗柯菲耶夫说起他最心爱的作曲家是海顿。我也很崇敬海顿,他的作品多么鲜活!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喜欢海顿甚于莫扎特。而其它钢琴家呢?他们常常忽视海顿,这多么可惜!
我都把莫扎特忘光了,是不是我脑子出了问题?这很可怕,我根本记不起来了。如何来演奏莫扎特?有谁能弹好莫扎特吗?演奏莫扎特的秘诀是什么?没有答案。同样的乐句在海顿和贝多芬那里再简单不过了,但在莫扎特写来就难得可怕,是难极了!我还没找到演奏莫扎特的窍门。
我不喜欢被弹滥的音乐,比方说肖邦的那首"葬礼"奏鸣曲,简直让我作呕! 虽然这是一个天才之作。我有太多其它作品想去弹,总比去弹人人都弹滥的曲目要好。不包括室内乐在内,我有八十首保留曲目。我以前习惯背谱演奏,但现在不这样了(李赫特晚年都是看谱演出)。首先,这样更加诚实:你要按照谱子精确演奏,但你不可能记住谱子上的所有指示,于是,人们就开始所谓"演绎"。我坚决反对!
(采访者:你的诠释经历过演进吗? )
如果有,我也注意不到! 我从未怀疑过:正道只有一条。为这个简单的理由,我总是仔细阅读谱子,任何曲子只有一种诠释方法。库特·桑德林这样说我:"他演奏得很好,但读谱更好。"
(采访者:为何你不经常和乐队合作? )
他们是要排计划的,而我却不行! 他们总说:"五年之内。"计划! 到处是计划! 也许这样不太公平,但在俄国只要他们想听我演奏,就会取消交响音乐会,让我上场,而这里(西方)却不可能。
我从不订计划,我随时准备在任何地方演奏。哪怕在学校,没有报酬。我也不关心是否在大音乐厅。他们总说我爱在小场子演奏,完全不是! 大的音乐厅总是被订满,当我想去演奏了,他们早就排了菲利普·昂特蒙!
如果事情都预先安排好,我总会让它泡汤。如果我自问:明天如何? 这样,那样,都行! 鬼知道我三年中会乾啥!
我很喜欢一个画家,他在俄国很出名,罗勃特·法尔科。他有次对我说:"绘画中最难的一种技巧" - 我觉得在钢琴上也一样 - "就是画一个完美的圆。"我曾去他那里上过几节绘画课。他当时说:"当你用双手同时画两个圆时,反而容易画得匀称。"这在钢琴上道理一样:一切都要匀称。他还说:只有当你刻苦劳作之后,那一刻才会来临,就如同水终于烧开一样,那才是最要紧的一刻。
合作
我常和穆拉文斯基合作勃拉姆斯,可他总想排柴可夫斯基协奏曲。穆拉文斯基,多伟大的指挥家! 你们都听过我和他合作的那个录音(指柴可夫斯基钢琴协奏曲)。
那么和卡拉扬的那个版本呢? 那里面有个大错! 就在第二乐章:华彩过后,呈示部反复,他一直保持那个音,不给我起拍。这家伙顽固透顶!
卡拉扬有时也有奇思妙想,比方说他指挥的马勒。可是在三重协奏曲(贝多芬)中他却严苛极了! 那次录音简直像打仗:卡拉扬和罗斯特罗波维奇是一帮,而我和奥伊斯特拉赫一伙对着乾!卡拉扬感到奇怪,为什么我总看上去闷闷不乐?因为这其中有些挺浅薄无聊的事情,奥伊斯特拉赫也不开心,而罗斯特罗波维奇总想出风头。卡拉扬对速度判断有误,我不喜欢这速度,奥伊斯特拉赫也表示反感。就是在第二乐章,罗斯特罗波维奇觉得排够了,卡拉扬按照他的一贯作风说:"行了,这样没问题!"
我说:"不行,让我们换个速度。"
"不,我们还有更要紧的事 - 拍照!"
在那张讨厌的照片里,他装腔作势,而我们像白痴一样在傻笑! 真恶心! 那天他是这么回答我的:"我可是个德国人。"
我说:"那我就是中国人了!"(在欧洲的漫画中,中国人通常被画成咧嘴赔笑的样子。)你怎么会喜欢这种人呢!
我很喜欢布里顿的音乐,我听过许多他的杰作:《麻鹬河》、《阿尔贝·埃林》,后者我还演出过,还有《旋螺丝》。我们是好朋友,在一起弹两重奏。我们在阿尔德堡现场演出过,双钢琴奏鸣曲(莫扎特),我和他只排练了三次,的确排得很少。
一次在奥德萨歌剧院前,当时街灯还没亮,我和一个人擦肩而过。他直直瞪着我,眼睛里一片茫然,呆滞无神。我认出他是肖斯塔科维奇,打心眼里不舒服。我知道他的歌剧,当时谱子已经出版了。作品里有股让人作呕的粘合剂的味道。他在场我就有点发怵,膝盖在打颤! 他很古怪:神经兮兮的,但认真得要命!是个大天才,却古怪极了,像个闷葫芦。他几乎是疯疯癫癫的。我不疯,我很正常,我只是有时希望我是疯的!
(尼娜:"肖斯塔科维奇第一次来我家,斯拉瓦对我说:'当代的柴可夫斯基来了'。")
我们很快成了熟人,可还称不上朋友,后来才成了朋友。那时我和奥伊斯特拉赫首演他的奏鸣曲。
了不起的小提琴家!他是最棒的!我父亲介绍我们认识时我才只有十二岁,他已经快十七岁了。他那么优雅,那么英俊,同时又和蔼可亲。后来我去听他的音乐会,什么样的发音啊!几乎举重若轻!没有多余的动作。奥伊斯特拉赫和我合作过多次,勃拉姆斯、弗兰克…… 在对弗兰克的演绎上,我们有些分歧:他觉得这是客厅音乐,而我觉得这是部神奇的作品,有普鲁斯特的笔触。尽管这样,我还是觉得我们录制的勃拉姆斯和普罗柯菲耶夫很不错。
(尼娜:和费舍尔-迪斯考合作就没这么简单了,对斯拉瓦来说很麻烦。这是因为费舍尔-迪斯考个性极强,斯拉瓦也是如此,他们总是很难合拍。他们举行的音乐会妙不可言,他们似乎都超然物外!)
这个人简直是个奇迹,无以伦比,不可置信!和费舍尔-迪斯考合作很难,他对歌词的苛求无以复加,想要和他保持和谐一致,他的伴奏者一定要稍稍等他一点。他的发音句读无比惊人,演绎沃尔夫则相对容易些。无论在交往和音乐上,我们都度过了非常美妙的时光。
如今,安德烈·加夫里洛夫是一个国王。他很幸运,总是能自得其乐! 这是健康的标志。不过倘若他能再谦逊一些,他会更加快乐。我们合作录制了亨德尔的组曲。当朋友们在听这张唱片时,我让他们猜这是谁弹的。很多人都会搞混。就连我自己,有时也会听不出两者之间的差别。光凭听,我甚至觉得加夫里洛夫弹得更有意思,尽管李赫特弹得毫无瑕疵。(这套亨德尔组曲后来被EMI收入廉价小双张的"强音"[FORTE]系列中发行)
退休
尽管我脾气不小,但我其实性子很冷,对自己总是有客观超然的看法。
如今我力不从心了,它已不在巅峰状态,无论脑子还是听觉都衰退了。可我还以为状态一流,而它已经一去不返了。我的听觉已经抓不住调了,我害怕再演奏了。现在我退休了。
我觉得很厌烦。我总体上讲的还是生活,而不是音乐。人生有太多的烦扰,世事纷繁。
我讨厌我自己,就是这样。
文字来源:東柏林地下黨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828568/discussion/180097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