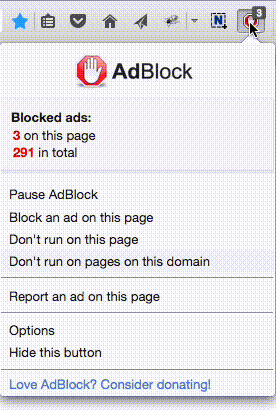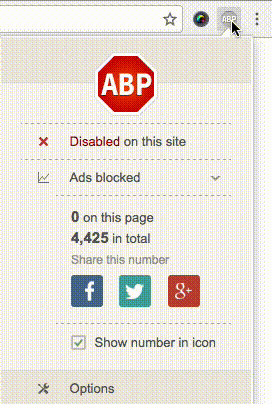母亲节有感 - 代八十行述 赵复三
大概因为生逢战乱, 小时候, 母亲记得家里谁过生日了, 就在晚饭时吃一顿面, 这就是过生日了, 家人彼此之间, 没有“送礼”的客套; 逢年过节, 家里也没有什么热闹; 由此养成了对节日的冷漠。成人以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家庭温暖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 不够革命化; 不顾家, 才是革命家庭的标记。文革以后, 家破人亡, 已经没有任何过节的心情。六十三岁以后, 漂流异国他乡, 只觉得有家的人才“过节”, 一个人过节,“心想便已事成”了。如今行年八十, 周围的亲朋过“母亲节” , 感染了我, 却不禁问自己: 划出日子来过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有什么是过去、去年、前年或大前年所没有的感觉呢? 想想,也还是有一些。
母亲从1891年出生,到1971年去世,活到八十岁 ,如今我也行将八十了; 心里经常想到母亲的一生。母亲总盼望有 一个女儿,可是她生了四个儿子。小时候,总听母亲的朋友们说,母亲好福气,有四个儿子! 我不懂得“福气”是什么意思,只记得六七岁时,常听见母亲说腰酸腿疼,叫我帮她捶捶,我便抡起拳头在母亲腰上捶,捶完这边,再捶那边。后来才听说“养儿防老”,母亲的“福 气”,是在后头。
一
抗日战争开始,天津很快便沦陷了。在那战乱的年代里,靠父亲一人在银行的薪水,维持六口之家的生计,每次母亲告诉父亲,家里的钱又用光了;父亲便板起了脸,怪母亲不会持家。然后,母亲便哭着,拿出家庭账本来让父亲看,钱是怎样用掉的。第二天,母亲还会委屈地和孩子们诉苦。我们孩子们亲眼看到,母亲每天清早起来,到小菜场买菜,到米店煤栈、买米买煤、买油盐酱醋、回家摘菜洗菜、做三顿饭、洗全家的衣服,缝孩子们衣服上脱落的纽扣,补全家人的破袜子,从天明忙到半夜,晚上孩子们没睡,要催孩子睡觉,孩子睡觉后,她才能戴上黑色的老花眼镜,在灯下缝缝补补;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一年四季,秋天要忙着为全家预备棉被和冬衣,夏天又要看天气晒衣服。我不记得母亲曾经穿过一双没打过补丁的袜子。父亲的绒布内衣内裤旧了、破了,母亲改小了自己穿; 母亲为孩子们织毛衣,可是她自己的一件咖啡色毛线背心穿了不知多少年,穿得毛都脱落,成为一个松松垮垮的线背心了。
在抗战期间,我们三个大孩子到上海读大学,父亲毕生靠自我奋斗,他的心愿是,孩子们长大后能靠自己的本事挣钱,不要靠别人,所以大哥读医,继承三叔。二哥读电机,我性情不近理工,只好读文科,四弟读中学,将来也学理工。四个孩子的大笔学费,全靠父亲筹措。母亲结婚时,大舅送的钻石戒指,她拿出去卖了,却从不告诉孩子们; 父母亲从不曾向我们叹过一个字的苦; 父亲倒向我们说过,他1914年靠清华公费留美,在美国和孔祥熙是同学,都在留美学生社团“成志社” 里面。
1919年回国后始终郁郁不得志,他的同学如陶行知、陈鹤琴、何廉,都在教育界。他为养家而从教育界转入银行界。抗战前,孔祥熙要他到南京国民政府做官,他想,做清官养不了家,做赃官对不起国,谢绝了。这是父亲以他生平对孩子们教育最深的一件事。我常想,父亲在辛亥革命时,曾经投效革命军,当过护士,而革命很快就烟消云散,他又回到南洋公学,此后不大热衷革命高调。1912年考入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1914-1919年到美国读书,回国又赶上了五四运动。1937年抗战爆发,我刚入初中。在家里,父亲为孩子们订了三份刊物: 一份是马国良主编的《良友画报》,一份是开明书店出版的《新少年》,一份是卢于道主编的《科学杂志》。我不安份,还从父亲床头翻看他买的邹韬奋《生活三日刊》合订本,《萍踪寄语》、《萍踪忆语》。
父亲在思想上给我的到底是什么呢? 概括地说,大概是两个方面: 第一,人生包括做人和做事,其中首要的是做什么样的人;其次,才是做什么事。父亲教孩子们的第二方面是: 运用理性、追求知识,奋斗自立,为国为民。
母亲在十九世纪末、出身於香港两代基督教牧师的家庭,读了四书五经 ,又读了洋学堂 ,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 ,却又具有现代知识。对我一生教育最深的到底是什么呢? 母亲是一个善良的基督徒,孩子们从小便跟着母亲进教堂,不是去拜菩萨烧香求什么,是去“敬拜神、听道理” 。小时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入大学后才渐渐明白,拜神就是教我知道,人的生命是渺小有限的,神是无限的,又是具体的,就是真、美和善。人的生命只有向着神才有意义。第二,基督教讲“爱” ,这是天地间最大的力量,基督就是把这作人的力量带到人间,因此是救世主,这是“敬神学道“的内容。父亲教我们要奋斗,母亲教我们要不狂妄,要自知自制,都是讲做人。
母亲教我的第二件事,就是要学二哥的“忠厚”。后来我慢慢明白,“忠”是对事,就是照着事情自身的道理去做事情,“厚” 就是对人,要宽厚。母亲把《论语》和基督教信仰非常自然地结合起来,《论语》主要是讲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 母亲则讲一个人要有爱心,要通情而后达理,这就是人的本性。她平日教孩子的也就是自己每天所做的。现在我才明白,其实母亲所教的就是从前中国许多地方、许多人家大门上的那副对联: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的道理,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在精神上能够挺立起来,首先是靠人内心的精神力量。母亲是这样教孩子的,她自己在坎坷的一生里,也是这样做的。
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中,1931-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入中国由胜而败的十五年是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在这十五年里,国?党政府虽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却因官僚统治的贪污腐败逐渐失去了民心,民心逐渐倒向共产党一边。这个转变,在抗战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地区,大概可以用1941年蔣介石在皖南包围消灭共产党的新四军作为一个分界线。在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半部地区,国民党政府的威信则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直到国民党接收大员到先前被日本占领的地区大肆掠夺 (勒索金子、票子、车子、房子等的所谓“ 五子登科” )和发“金圆券”,骗取民间余剩财富,造成经济金融大崩溃,使国民党政府完全失去了民心。这是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崩溃如此之快,超出共产党原来估计(内战还准备再经10-15年)之外,共和国于1949年得以成立的政治原因 。中国的中间阶级和大部分知识分子也是在此期间失去对国民党政府的信任,而逐渐转向共产党。从父亲和母亲身上也可以看出来。父母亲都不是关心政治的人,他们由于经济地位和所受教育,自然倾向于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正统观念。
但是,抗战胜利后,张家口一度解放,父亲不知经过什么关系 (当时我们在上海),以天津金融界人士的身份秘密到张家口共产党地区去参观。他后来告诉我们,共产党当局要他留在张家口,他说要挣钱养家,不肯留下; 却答应在家里掩护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后来,的确有一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到天津,在父亲掩护下,在我家住了一年多。这在当时是“杀头之罪”,父母亲却甘冒杀头之罪为共产党效力。家里四个儿子,也都随着进步学生运动倾向革命,支持反蒋运动。二哥在大同大学读电机系,因为办学生食堂,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抓进监牢,关了半年多才放出来,1946年转学燕京大学,1949年毕业,志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被分配到辽宁阜新煤矿。二嫂崔兰芳是燕京音乐系毕业,也跟二哥一起去了。
1949年共和国成立,当时人们期待着的是: 打倒蒋政府,建设新中国,只是不知道,将来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 根据《新民主主义论》,耕者有其田,还要发展工业,建设由五种经济成份组成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在此基础上,由共产党领导、多党联合执政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文化; 为此各政党制定了具有宪法职能的 《共同纲领》。按照1949年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天津和北京所作的讲话,这个纲领要贯彻10-15年; 然后各政党再协商怎样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可是,才两年,这个当初被宣传为“庄严神圣”的共同纲领就被掌权的共产党践踏在脚下了。1951年,全国农业开始成立互助组、初步合作化;1953年,公布“过渡时期国家总路线”,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全国农业合作化,全国私营工商业也全面合营,“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在文化教育领域,从1949年展开“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1951年,以“反对亲美、崇美、恐美” 名义,开始长期全面批判西方文化。同时,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进行批判。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文学、历史、哲学只准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优生学、心理学等都停办,大批教授不能开课,全时间学习改造思想。1954年,在学术界批判胡适。1955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在文艺界发动反对“披着革命外衣” 的胡风反革命集团,被划反革命分子和有牵连的达两千多人。到1957年,全面打击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的 “资产阶级右派” ,五十五万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敌人”,这时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全面完成,才公开宣布,从1949年起,全国便已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毛主席是绝对领导,毛泽东思想是绝对真理,由此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用林彪做最高领导接班人,以军队砸烂原在刘少奇主持下的党政机构, 另建党政合一的革命委员会。在经济建设方面,实行“抓革命、促生产” 的方针,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1958年推行大炼钢铁、生产翻一番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 ; 取消商品经济,实行产品直接分配,造成两三千万农民的死亡。 大跃进失败后,毛又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为纲”,发展为1966年开始、持续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而自行瓦解的文化大革命。
这一年来,自己回顾二十世纪下半叶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得到一些新的认识: (1)任何政治运动、任何政党、任何政权、任何政治人物,掌权之前为贏得大众支持而把人民民主说得信誓旦旦,上台后,背弃诺言,便暴露出这并不是一个严肃的政治家,而是政治野心家加骗子。封建时代的野心家把自己说成是“奉天承运” ,当代的政治野心家则把一种新鲜政治理论说成绝对真理,其实也无非是表明自己“奉天承运”,而历史的事实和实质是无法涂抹掉的。(2)有的历史家割裂历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毛泽东个人的事情,又把毛的这一段历史和在它之前的历史割裂,想以此掩盖抹杀历史的延续性,只是徒劳。任何人仔细读一下历史,便会发现从49年到76年,毛所做的就是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路线,在他来说,这是一贯的。(3)从49年起,毛推行“阶级斗争为纲” 的路 线 , 所抓出来的一批又一批的 “敌人” , “现行反革命分子”,包括一个又一个的 “反党集团”,绝大部分是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如康生、江青之流制造出来的。《论语-为政》篇教人“温故而知新”,重温历史,是为了将来。《毛泽东选集》里, 曾经教导人采取一种观察历史人物的办法,从蒋介石的的过去就可以认识他的现在和将来; 那时蒋介石掌权才二十年,此后毛泽东则掌了三十年权,是否也同样适用这种观察方法来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呢?
1982年,邓小平主持制定中共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在毛死后再次肯定,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全党智慧的结晶。换句话说,就是宣告: 毛泽东思想乃是中国共产党全党的思想; 再换句话说就是: 中国共产党奉毛泽东思想为圭臬这一点不改变(邓已经抛弃毛的封建社会主义路线。《决议》的意思大概是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因此领导层无论怎样走马换将,中国也不会有实质的改变。
历史总要把一般和个别结合起来,才不至以空洞的史论代替历史——这恐怕是五十年来中国标榜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的一大缺失 — 把本来有血有肉的人的历史变成历史家的空泛史论。这里试举我一家的历史,为上面所说的历史做一个例证。在我们家里,自49年天津、北京解放,父亲便失业了。他曾表示希望做任何对人民有益的工作,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回答说,旧知识份子需先在革命大学学习, 经过思想改造,才能为人民服务。父亲便要求到革命大学去学习,回答说,革命大学学员最大年龄是55岁,父亲已经56岁,所以已经没有资格进入革命大学。他从49年失业,1957年二月去世,四个月后便开始“反右斗争”了。我心里庆幸,如果父亲还做事,或活到“反右斗争”之后,恐怕难逃“右派”的命运: 以他的暴烈性情,想不通的事情便要反抗,说不定会“升级” 成为“反革命分子”。父亲去世那年才65岁,后来我每次读到说有些人“生逢其时”,便会想父亲在反右斗争前夕去世,真是“去逢其时”。儿子为父亲去世而心里庆幸,这种“不孝”恐怕是只有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的特殊国情。
1957年的中国反右斗争是毛有鉴于波兰、匈牙利国内大规模反对共产党运动而在中国“防患未然” 的措施。1957年,各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为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而矛盾尖锐化。这是1958年,毛泽东在中国发动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要求工农业生产翻一番,结果带来大失败的国 际背景。1959年毛坚持还要“持续跃进”,把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 的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随后全国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 二哥所在的阜新煤矿,为贯彻“持续跃进”而乱挖乱采,造成矿井爆炸的重大事故。二哥被矿务局领导指派为抢救组组长,下矿井抢救伤员、恢复生产; 在井下瓦斯窒息中坚持工作了五昼夜,终于身体不支被抬到地面,送入医院,不到二十四小时便去世了。
那年,他和二嫂都是39岁,两个女儿,大的五岁,小的一岁。那时,母亲正和二哥住在一起,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在自己眼前去世,对一个年近七十的母亲,这是心如刀割啊。 二哥去世后,她虽然回到北京,二哥留下的寡妇幼女,孤苦怜仃,却还在矿山的艰苦环境里挣扎活下去。那时我自己也在反右之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迫要交代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想,被整得死去活来。运动过后,已是第二年春天,我到阜新去看望二嫂和侄女们,听二嫂讲,冬天来临,每户分配几十斤过冬的大白菜,她下班回来,晚间一个人拿铁锹,在后院冰冻的土地上,一锨一锨地刨菜窖;和二嫂、侄女们一起,到二哥的坟堆上去痛哭一场。
二嫂的父亲是入中国籍的南开大学英语教授Percy B. Tripp (中国名字是崔伯,号仰西,他是美国弗吉尼亚州人,五四运动时到中国教书,娶了中国妻子,入了中国籍,是周恩来在南开大学读书时的英语老师; 抗战时日寇占领天津,他虽已退休,还受尽日寇侮辱; 抗战胜利前后在天津去世。五十年代,周恩来的南开老同学曾对周提到崔教授,周恩来说,“记得,他是美国人,娶了中国妻子,入了中国籍,他是爱中国的”)。文革时,二嫂在阜新被诬为美国间谍,被斗争得死去活来,逼她交待罪行和同谋,最后逼得她酗酒自杀。去年二嫂的五妹(小时候我们叫她五姑)从旧金山回国,到阜新去看望两个外甥女,才知道,文革时, 二哥也被诬,革命造反派把他的坟挖开,把二哥的尸骨拋出来。 二嫂带着两个女儿,在坟园外面,把隔墙拋出的自己丈夫、我二哥的尸骨一根一根拾起来,想再埋到别处,可是谁也不肯或不敢收留,经过四次求告,才把二哥的遗骨重新埋下; 我的七岁的小侄女,经受不住这个刺激,一时神经失常了。 二嫂只求一死,天天叫大女儿为她买白酒,十一岁的大侄女,天天哭着不得不为母亲去买酒,又哭着求母亲不要再喝酒。最后,二嫂还是肝癌去世了。两个女儿,就此成为孤儿,而且因为父母都是“美帝特务”,朋友都不敢伸出手来援助; 姐姐带着妹妹,咬牙往前走; 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得比别人好,才能贏得一点同情。我流着泪听,听得心都碎了; 同时又想,幸亏母亲在1971年去世时不知道,她的忠厚、忠心为国的二儿子、儿媳全家四口,最后落得的是这样的下场。但是,她自己也没能逃过文革这一劫。
二
文革开始发动时,我还在山西参加农村四清运动;被叫回北京,返京一周, 便在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被革命群众定为牛鬼蛇神,实行专政,但还可以每天回家。当时,大哥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已经工作十年; 他虽然自幼便有哮喘病,容易累,一犯喘便无法睡觉,但他医术好,而且对病人热情,不仅是一个好医生,而且从学生时代起,便是爱国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工作后,在协和医院里,又是紧跟领导的积极分子。他不懂政治,没有想到,这样一来,自己便成了文革中的箭靶子,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他热爱业务,被说成是“走白专道路”; 他关心病人,被说成是“拉拢病人”,紧跟领导被说成是“拍马屁”;他带头写一本《性的知识》,内容无非是医科教科书上的基本常识,却被说成是“毒害青年”,最后,被归结成“十大罪状”。大哥从来未曾经历过这样粗暴的诬蔑,而文革却是 “伟大领袖英明伟大的战略部署”,“要把一切暗藏敌人统统揪出来,打翻在地, 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他告诉我,医院里革命群众给他定了“十大罪状”,问我“怕不怕?” 我说,“不必怕! 如果能成立的话,一条罪状就能够置人于死地,现在说你‘十大罪状’,就表明他们自知站不住脚。”这话才说了一个礼拜,我就被关进了牛棚,昼夜受监视。当然不准回家,除审讯我的专案组外,不准接触任何人。那时,母亲和大哥住在一起,侄女已经离家闹革命去了,家里只有母子二人相依为命; 大哥承受不了人格侮辱,宁死不屈; 此后不到一个月,便在一个夜晚自杀了。那时,大哥和妻子离了婚,自己带着一个女儿,大哥去世,女儿也成了失去家庭的孤女。我当时被关在牛棚里,当然毫不知悉。
直到两年多以后,被命令回家收拾行装、准备下乡劳动改造,回到家里只剩母亲孓身一人(那时她78岁)。屋里的家具都卖了,只剩下一张床 ,一张小饭桌,和两把椅子。我问母亲: “大哥呢?” 母亲说: “去世了。” 我又问: “怎么去世的?” 母亲只说了两个字: “自杀”。她一生从来不说硬梆梆的话,这一次,说的时候,眼里没有一滴眼泪。我知道,母亲的心又一次被碾碎了;碎得流不出眼泪了。
1970春,我作为“有代号的潜伏美蒋特务、还拒不交代罪行” 的阶级敌人,在军宣队领导下到河南南部、隔淮河与安徽凤阳相对的息县 (当地人称 “ 蛤蟆坑” )入“五七干校” ,继续“交代罪行”。我只能服从前去,但是母亲怎么办呢? 我把所有的钱都交给母亲,又到居民委员会,请一位工农阶级出身、革命工人的家属来帮母亲买菜、做饭、洗衣服; 再托从前基督教会的老朋友常去看望母亲。 临走前,和母亲一起吃饭,我对母亲说: “妈妈,你吃啊!” 她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说:“你吃啊!”两个人,谁都吃不下一口饭,但都怕彼此伤心。
1971年春,母亲写来一封信,说居委会认为她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家属,强迫她搬家,腾房子。搬家时,她跌倒在地上,从此只有卧床; 帮她的工人家属,把她放在衣柜里的钱都偷走,然后就不来了。四弟远在湖南,我向军宣队请假回京看望母亲,军宣队只给三天假,路上走了一天。回到家里,母亲躺在床上,已经皮瘦如柴,眼睛也深深凹了下去。在家只能住一天,又要赶回河南去。临行前,在母亲床前,她把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的手,放在我手里,用微弱的声音说: “我想哭,可是眼泪都已经哭干了” 我只能轻声安慰母亲说: “妈妈,我还会回来看你的。” 可是在我心里,我知道几时还能回来吗?
回河南的火车上,想起从前人家说母亲“福气”,生了四个儿子,可是,在现实生活里,多一个儿子,不是多一重对母亲的心灵折磨吗? 没有孩子,母亲也受苦; 有了孩子,母亲也受苦,难道生命只是为了受咒诅吗? 母亲的眼泪,不就是这样哭干的吗? 回干校一个礼拜,母亲便去世了。 我又请假回北京,到母亲床前,俯下身去,在母亲额上亲吻一下,用手轻轻帮她合上眼睛。我只能含着眼泪感谢上苍,怜悯母亲,把母亲接回天家去了。母亲离世时,身旁没有一个亲人,是我不孝; 我也没法告诉四弟,是我这做哥哥的“不悌” 。我怎样对大哥、二哥、四弟交待呢? 母亲去世以后,我也只剩自己孓身一人,觉得在世上真正成了一个对母亲有罪的孤儿,那年我45岁。
三
没有必要多说我自己的小家是怎样在文革里、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下被砸成齑粉的,记得好像是美国汽车大王亨利- 福特曾经说过他的人生格言是: “永不抱怨,永不解释”; 这也是我从父亲身上学到的人生原则,重要的是自己怎样努力与命运搏斗,而不是自怜自艾;一个人总要有一个人的骨格。但这次母亲节,我也对妻子讲到,两个女儿的母亲、我的前妻瞿希贤是毛泽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牺牲品。
她高中时代为参加抗日,从上海离家到内地去,历尽干辛万苦,…… 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沉重打击下,回到上海家里,以后入大学,参加革命歌咏运动。她是一九四九年后,在旧知识份子里,按《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而重点培养出的一个样板,因此被捧了起来(其实,从前在延安也捧过丁玲; 1952年中国当局推荐丁玲领受苏联的斯大林文艺奖金;1957年又把她划为右派),文革之前,江青似乎对瞿希贤有所垂青,情形我不清楚。1966年文革开始后,江青又狠狠打击她。一个夜里,几个军人突然敲门进来,既没有说是什么单位来的,也没有说瞿希贤犯了什么罪,便把她抓走了。第二天,我送脸盆牙刷到北京监狱去,监狱说并无此犯人; 从此没有半点音讯,连生死都不知道,达十年之久。
两个女儿,大的初中刚毕业,15岁,小的13岁,刚进初中二年,从来都是同学中的佼佼者,一夕之间,父母都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孩子从小只知道要“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这时要“革命”,自然要划清与“反动” 家庭的界限,成为无家的孤女,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当农工。大女儿出发前,我还未被关进牛棚,心想不知孩子要去多久,他们没有了妈妈,我就是妈妈,一心为孩子准备一年四季的衣服,孩子怕冷, 我居然能为她买到一条毛线裤。到她走时,衣服塞满了一大柳条包。孩子已经好久没有和她的“黑爸爸” 说话了,看着那大柳条包,说了一句: “像给我预备嫁妆哪!”,这是多么温暖的一句“谢谢”啊! 我把柳条包用绳子缚在自行车后面的架子上,孩子推着车,我跟在后面默默地走,直到她说: “你回去吧!” 我才站住, 还是默默地望着她的身影,直到看不到为止。大女儿初去黑龙江时,因是“黑五类”子女,兵团不收; 她天天上工,却没有粮票、工分,生活全靠同伴们接济,经过半年,才被接受。
小女儿不久也去了,这时,我刚被关进牛棚,想黑龙江天气冷,请求看管我的专案组长,准我买两磅毛线,照从前母亲教我打毛线的方法,用笨拙的手指,一针一针,想给她织一个用元宝针结的厚围巾。元宝针比平针难,我从来未曾织过毛线,常常织错,又要拆了重来; 我就一遍又一遍地织,一面织,一面流泪。想起从前孩子刚进幼儿园的时候,我为她买过一本小人书,题目叫“我不哭”。没想到,这本小人书像是总对着我说: “不哭! 不哭!”。在为孩子织围巾时,一面织,一面流泪,一面对自己说: “我不哭,我不哭”。就这样,围巾终于织好了,又请求专案组长,准我去一趟邮局。寄出后没有回音,也不知道有没有寄到,也不知道有没有给她带来难处,因为她当然要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
十年後, 她回到北京我才知道,在黑龙江,冬天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几十度,大年三十,别的青年都回关内探亲去了,一间大宿舍,只剩下她一个人。夜里,天寒被薄,她只有在被里缩成一团,这就是自己一个人的“团圆年”。
1976年,瞿希贤又突然回来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连同十年经历,我都不敢问。当时,周恩来已经去世; 文革已入颓势,却还在进行。我从住牛棚的经验知道,即便未被关进监狱,实际上全国就是一座大监狱: 即便从监狱放出来,实际上也还是专政的敌人。那个年头, 一切都是阶级斗争。我又是“长期潜伏的美蒋特务”,连女儿都恨自己,为什么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在文革的岁月里,遭到这样打击的家庭,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朋友,自杀的有多少,我没有计算过; 因为没有那样刚硬的心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已被锁定是“敌人”,面前只有三条路: 跪下求饶、做割舌金丝鸟,不准唱歌,但还可以舔统治者的屁股,自杀,或四散逃生。在我家里,既然两个大人都已被无产阶级专政锁定了是“敌人”,只好四散逃生,四个人里,能活一个算一个吧。此后,帮孩子重新读书; 最后女儿两家人移居国外。九十年代直到现在,女儿们每年回北京看望妈妈。我知道,我的前妻和两个女儿,终生都带着无法愈合的心灵创伤,这也是我背负罪孽的一部分。
四
在美国,母亲节时的贺卡里面,有一种祝词写的是: “亲爱的母亲: 你既能把我拉扯大,也就能够承受一切!”今年母亲节,我不由地想到三位母亲,他们都把孩子拉扯大,也都承受了命运加给她们的一切。但是,母亲对我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总在我的耳边,在我的心上: “我想哭,而我的眼泪已经哭干了。”
我们家里一直相信,新中国是给人民大众带来幸福。这一家,三代人,从父亲母亲、到我们弟兄,到下一代的女儿们,其中每一个人都照着时代的要求,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去为大众做有益的事情;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 这是历史的偶然吗? 是个别人的失误造成的? 抑或是命运呢?
四弟曾在文革后,写信告诉从前曾在天津由父亲掩护了一年多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李先生,我们这一家人在文革中的遭遇。李先生后来大概是个不小的干部,还是一位念旧的人,回信给四弟说,他自己在文革中也同样受到清算,但大家还是以大局为重吧。四弟把这封信复印给我。我感念这位李先生的好意,也知道,许多好心肠的人都是这样看待过去五十年历史的。我也抱著同样的心情,看涉及个人的事是小事,应该“顾大局”。
但接下去想大局时,却不得不问: 什么是大局? 人民大众遭受苦难是大局,抑或保住共产党掌权是大局? 究竟顾哪个大局要紧呢? 两千三百年前的孟子懂得“民为贵,社稯次之,君为轻。” 可惜,共产党里,那么多俊彦之士,一旦取得政权,就把“民贵”的道理变成愚弄百姓的空话了。这是历史的规律呢? 抑或是某些人的愚蠢呢? 或是某些人的罪恶呢? 或是一些人的罪恶又加上一批人的愚蠢,便构成这段历史了呢?
而毛泽东是把这作为他一生所做两件大事之一来炫耀的。在西方,把古希腊时代写人与命运搏斗看为希腊文学艺术的高峰; 可是,2500年后的人民中国,怎么伟大领袖引为造福中国和世界的丰功伟业,到他死后还不让人民说出来呢? 是为了谦虚呢? 还是为了畏罪而涂脂抹粉呢?
从前,我也读过一些共产党员写的东西,如红军司令员方志敏被逮就刑前写的 《可爱的中国》,眼前的这些党员和先前的党员怎么如此不同呢? 说这些,并不是为了想在当今唤醒什么人,若那样存心,就会被认为是在搞“反革命颠覆” 性政治活动了。而我始终不是,也拒绝做一个政治人物。写出这些,只是为让亲朋友好知道我还没有痴呆,生在这样一个时代,所能做的大概只有为二十世纪中叶多少人曾经废寝忘食、日夜奋斗、寤寐以求、渴望来到的“新中国”做一点历史的见证,供后来若干年之后,对历史有一点好奇兴趣的人提供一点了解的线索而己。
…… 十五年前,在天安门事件后,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职,移居国外。1990年,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我这样一个已经退职的人定罪,把我钉进了棺材,我却还挣扎伸出了一只手。前不久,有朋友说我:“太理想主义了”。我想,大概是这样,一个已经被钉进棺材十五年的人,还坚持从棺材里伸出一只手,想抓什么呀?大概是想抓住那个“美好人间”的理想吧。这大概是我从母亲那里承受的最本能的一点。母亲活到八十岁,亲眼看到两个孩子在她眼前死去,第三个孩子被送到农村去改造,不知还能不能见面,最后,还有一个孩子,当时却连下落都没有了。她的眼泪哭干了,但是,心里还是想哭,因为亲情是人间生离死别和理性所割不断的,它还在心里,涌为泪泉,这亲情大概也就是维持我生命的力量。母亲把她干枯的手放在我手里,我用双手捧着,知道母亲把她的心、她对四个孩子的爱都放在我手里了;这双手张开的地方就是母亲的生命在人间的最后一块立足之地了。母亲去世时,我觉得自己的一半随着母亲,永远去了;而母亲去世后,我又觉得母亲的爱推动着我,要我继续她的生命而活下去;母亲的爱就是孩子的生命,母亲把她的爱放在我手里,这就成为我的生命。
可是,我活一天,就不能不继续体验人生,不由自主地要问:我所经历的一切是为什么?母亲不仅为孩子们痛苦,她还有自己安身立命的信仰破碎的痛苦。她相信,世上总是好人多,人人努力,社会总是在进步,一个人全心全意为家庭、为社会大众,上天不会亏待;可是她自己的路怎么越走越窄呢?日子怎么越过越苦呢?这是我从母亲毕生的眼泪里尝到的辛酸滋味。母亲没有得出“为什么”的答案,要我继续活下去,大概就是要我继续想她未能找到解答的问题吧。痛苦迫使我思索;迫使我问:“为什么”;迫使我到中外历史、哲学、思想史中去求解答。我发现,痛苦的不仅是我,还有比我更难的。因思索而获罪:在获罪中思索,这似乎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无法逃脱的命运。……
==================================
世人对赵复三知者不多,引用维基百科作一简介
赵复三 (1926年-2015年),上海人,194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随后任职于北京基督教青年会。1950年7月,时任北京青年会副总干事的赵复三,成为《三自宣言》的40名发起人之一。此后,赵复三出任中华圣公会牧师、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总干事、燕京协和神学院教务长、北京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
1964年夏,赵复三突然作为革命干部奉命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负责批判神学的任务,(其批判的成果就是《基督教史纲》,用杨真笔名发表,1979年,三联书店发行)。从助理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到1980年代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和党委副书记。并与赵朴初、赵紫辰合称中国大陆宗教学界“三赵”之一。
1980年代,赵复三出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三届、第四届副主席。赵复三又在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委员。又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派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9年六四事件后,赵复三在巴黎公开遣责中国政府动用军队镇压学生,1990年六月被撤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此后赵复三在美国南方一所大学任教。
赵复三退休后,与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退休部门主管陈晓蔷结婚,定居耶鲁,并翻译《西方文化史》、《西方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等著作。2015年7月15日,在美国康州病逝,享年89岁。他的朋友,学者丁伟志、何方等人发布讣告称:“在长达26年流离的晚年生活中,赵复三先生不计世事浮沉与荣辱得失,...... 始终放心不下的是中国文化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命运。”“这样一位终生热爱祖国的人,却最终未能叶落归根,埋骨异邦,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他所在时代的不幸。”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